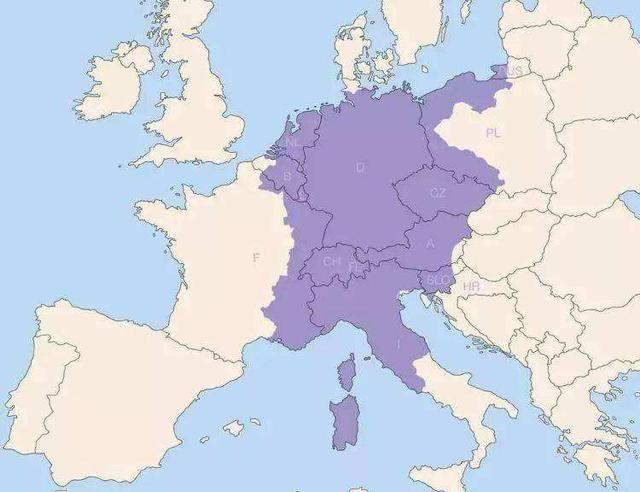判断中国是否有条件科学合理地达到排放峰值和实现倒逼机制,需要统筹考虑“能源-环境-经济”三者关系。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11月12日,在中美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中国首次提出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值,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此之前中国碳强度指标的承诺是相对减排,只要GDP增长,二氧化碳排放会随之增长,只需要增速减缓就行。这一次则是绝对量减排的承诺,2030年碳排放峰值将成为倒逼机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意义重大。
当前面临的雾霾环境进一步增强了国内减排的动力。雾霾治理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早日出现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通过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反映环境和资源稀缺成本,倒逼煤炭消费峰值尽早出现。中长期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煤炭替代导致的高能源成本问题。

排放峰值可能提前出现
中国出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基本条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品种必须至少一个出现峰值,从而抵消其他两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由于目前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65%以上,煤炭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较大,而且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将持续增长,所以中国的二氧化碳峰值需要以煤炭消费峰值为基础,也就是说,必须先出现煤炭消费峰值,然后用煤炭的减排来抵消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增长,从而得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
煤炭的消费峰值如何出现?随着雾霾成为当前举国困扰的难题,雾霾治理无法回避。中国大面积雾霾的主要原因是巨大煤炭消耗并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雾霾治理的关键是煤炭替代,这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正常的雾霾治理强度下,中国煤炭消费峰值将在2023年出现,消费峰值为45亿吨;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28年达到峰值130亿吨。虽然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二氧化碳峰值的时间,包括能源价格改革的进度、碳税和碳交易的实施等,但雾霾治理对二氧化碳峰值的影响较直接。

加大雾霾治理力度,碳排放峰值甚至可能提早出现。通过更严格的雾霾治理措施,高耗煤企业将被加速关停或被较高的环境成本逼停,从而使煤炭替代的进程加快,二氧化碳峰值也就会更早出现。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通过更严格的雾霾治理措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峰值时间可能分别提前到2020年和2024年,峰值分别为42亿吨和117亿吨。
国际经验表明,美国的煤炭消费在2005年之后开始下降,其二氧化碳在2007年达到排放峰值。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做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的承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的页岩气能够有力地替代煤炭。但更主要的是煤炭消费出现峰值。在中国的条件下,煤炭消费峰值之后的4~5年内出现二氧化碳峰值,应该是预期之中的。
因此,我们的预测跟这次中美联合声明的承诺基本一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煤炭消费峰值和二氧化碳峰值分别是2023年和2028年;如果加大雾霾的治理力度,倒逼能源结构加速变化,峰值可以提前,分别是2020年和2024年。如此,二氧化碳峰值在2030年之前到来是有可能的。

实现目标取决于三大因素
对于中国来说,以往的“低碳发展”是自上而下的事情,民众觉得与之关联不大,参与的意愿和积极性可能不高(包括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而雾霾治理的诉求则是自下而上的,在雾霾的大背景下,民众和企业有参与的共识和动力。但要实现煤炭消费峰值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需要有足够的清洁能源来替代煤炭,而替代能源必须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煤炭替代的路径比较清晰,短期的替代主力是天然气,中长期则需要发展清洁能源。因此,伴随碳排放峰值承诺,政府还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左右,而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9.8%。
目前水电占一次能源不到8%,受制于资源条件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即使装机发展较快,未来水电所占的比例也难有比较大的提高;风电太阳能目前比例很小,2013年为一次能源的1.3%,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对煤炭进行有效替代;而生物质、地热等的占比更小。

二是成本问题。较近的“APEC蓝”说明了雾霾治理技术上没有问题,关键是愿意付出多大的成本。煤炭消费峰值与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有直接的关系,与能源成本也有直接关系。无论短期的天然气替代煤炭,或者中长期清洁能源替代煤炭,都会面临能源成本增加的问题,因为其他替代煤炭的能源品种,都比煤炭贵。
三是煤制气和煤制油的发展态势。煤制气和煤制油是煤炭消费峰值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较大不确定性。即使在严格的环境治理约束下,煤制气和煤制油的规模发展将使得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出现大幅度提高,对应的峰值时间也向后推移。比如,煤制气得到的天然气属于对煤炭加工后的二次能源,其原料是煤炭,煤制气本身是一个高耗能的生产过程,意味着更多的煤炭生产同一单位能源产品。从全国范围来看,煤制气和煤制油不能达到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带来的能源安全隐患,以及其他清洁能源在资源和利用上的成本制约,实现有效煤炭替代和二氧化碳峰值目标,可供选择的空间似乎不大,因此,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发核电对中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选择。满足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左右的承诺,核电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核电发展可以同时满足替代量和成本问题。
2013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1461万千瓦,仅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2%,发电量也不到2%,而美国核电发电量占19%,相比于法国等核电大国的差距更为明显。统计表明,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8台,加上目前已投运机组,总计装机容量约4800万千瓦。考虑到核电建设周期至少6年,即使2015年前有新的机组开工,乐观估计到2020年核电投产装机5800万千瓦,估计能占到一次能源的3%左右,核电发展空间很大。

按照一次能源中20%清洁能源的承诺,根据目前能源行业发展和政府政策状态估计,2030年中国清洁能源的结构可能是水电8.5%,核电6%,可再生能源5.5%。意味着届时中国电力结构将可能有4.2亿千瓦的水电,3.1亿千瓦的风电,1.9亿千瓦的太阳能,0.2亿的生物质能,以及1.3亿千瓦的核电。
统筹考虑能源、环境与经济
APEC会议期间,能源局提出到2020年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同时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包括到2020年争取建成2亿千瓦风电装机和1亿千瓦光伏装机,目标是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5%。按照目前天然气国内生产、购气合同以及管网建设情况,到2020年占到一次能源9%应该是可能的。
#p#分页标题#e#而今年9月能源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力争使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62%以内。按照这一比例,石油的空间就只有14%了,可能性不大。因此2020年的煤炭占一次能源的份额应该更低一些,可能会在59%以下。

雾霾治理从技术上说没有问题,关键是愿意承受多大的成本。不同雾霾治理强度对应的能源成本不同,对产出、就业等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需要分析环境治理的宏观经济影响,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来考虑该环境治理强度是否可接受。
我们的研究说明,即使采用严格的环境治理强度,使得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峰值时间提前到2020年和2024年,就业仅下降0.01%,对应的GDP下降0.67%。因此,对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对产出的影响也不大。
由于不同区域环境治理强度的差异,中国煤炭消费峰值和二氧化碳峰值的实现路径具有“分区域实现峰值”的特点。雾霾治理重点区域(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将在2017年达到煤炭消费峰值,2022年实现二氧化碳峰值。但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投入,减少重点区域煤炭消费的直接后果是,增加其他地区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使得这些地方峰值后延。

因此西部加速污染趋势不可避免,但有效的政府政策可以降低西部环境污染程度。一是针对西部当地的生态环境,需要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即西部能源输出得到的资金,应该更多回馈到当地生态保护,以降低能源开发所导致的环境影响。二是保障能源输出的财富向一般老百姓转移,通过西部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使得他们可以改变能源消费方式,更多地利用清洁能源,更快脱离传统的煤炭消费,从而抵消环境污染。
要判断中国是否有条件科学合理地达到排放峰值和实现倒逼机制,需要将中国的“能源-环境-经济”三者全局归拢起来考虑,这能够更好地兼顾决策过程中发展模式平稳转变的问题和识别环境治理风险,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能否有效落地和执行。(林伯强,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