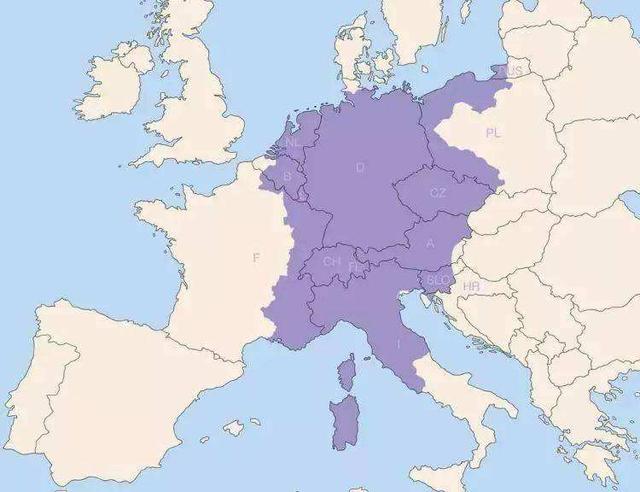到医院,医生说看一眼(我妈的)伤口,我下意识扫了眼纱布,立刻觉得天旋地转,晕倒的瞬间听见大夫问:“你们俩到底谁是病人。”
天津网讯 每日新报评论员 王晨辉 我妈是个铁骨铮铮的女人。
晚上我还没下班,儿子土土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说外婆把手烫了。我赶紧往家奔,我妈一边看电视一边俩手抓着生鸡腿,地下塑料盆里还有血水。作为儿女赶紧嘘寒问暖,她一甩头,眼睛都没离开电视:“盛面汤,盆边大概蹭了油,一滑差点掉地上,我给接住了,汤洒手里了。”听着云淡风轻,不就洒点面汤吗,可是手又红又肿离开冰就不行。我说去医院,我妈说:“去什么医院,到那儿也没治,看会儿电视就好了。”
咱家里冰箱从来没有冻点冰块的习惯,压根就不是那种特别洋气的家庭,就连去个快餐店要个可乐也必须提醒服务员“不加冰”!家里放冰块的地方早就让我摆上冻饺子了。所以我妈只能拿冻鸡腿给自己的手保鲜。

电视里在放农业致富的节目,满屏幕黑乎乎的蛤蟆在蹦,她特别热衷提高创业节目收视率,看看别人家孩子怎么发家的,然后给我们励志。俩鸡腿快让我妈捂熟了之后,我又拿出了一袋排骨,当冰块用!争取把饺子留到较后。家里的毛巾全都蘸水,然后往冷冻室扔。一直到深夜,地上摆满了解冻的大鱼大肉,电视里歌舞升平,看着跟要过三十儿似的。
我妈很自豪地张着俩手在我们眼前晃:“也就是我,手上皮厚,要是别人那嫩手早完了。”我们赶紧点头,满脸的心服口服。我妈愣是以自己的钢铁之躯扛过了一场烫伤,转天手掌上很多涨起来的水泡。
手刚好,忽然一天,我妈进家门就撩裤腿儿,我赶紧问:是摔着了吗?她一屁股坐沙发里,弓起的膝盖两块擦伤,都露红肉了。经过了多少年的外科家庭急救训练,土土迅速打床上拎起一个荞麦皮枕头就给扔微波炉里了,他说,必须热敷!在枕头快到再微波就得自焚的温度,土土拿棍子给它挑出来,在我妈裤子外边一裹问:“热乎吗?”我妈铁骨铮铮的劲头儿又来了,骄傲地说:“地上突然来个坡儿,我脚还没落地儿,身子先到地儿了。也就是我,骨头没事,换别人腿早断了。”我们集体蹲在纱布旁边,使劲点头,心里那个后怕啊!

还有一次,早晨听见我妈在厨房里“哎哟”。这动静有点不对,她的一惊一乍平时表现在看恐怖片上,那叫声比情节提前,特别给影片出效果,可厨房里也没电视啊。我开门一看,我妈拎把菜刀正看烧饼:“我打算烧饼夹牛肉的,可切烧饼劲用大了,血掉烧饼上了,你们还能吃吗?”我都不敢看了,这简直就成鲁迅作品了。
我妈把一管牙膏都挤在伤口上,这次必须去医院缝针了,车限号,我叫专车,我妈从容地用小拇指挑起自行车钥匙:“没几步,你骑车驮我去。”到医院,医生说看一眼伤口,我下意识扫了眼纱布,立刻觉得天旋地转,晕倒的瞬间听见大夫问:“你们俩到底谁是病人。”我妈怎么缝的针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躺在外科病床上等虚脱的劲儿过去。
什么女汉子女强人这些形容词到我妈这儿得主动不好意思,我妈就是罩着我们的一片天,让那些磕磕碰碰也不要打扰她吧,有她在的家才是个团圆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