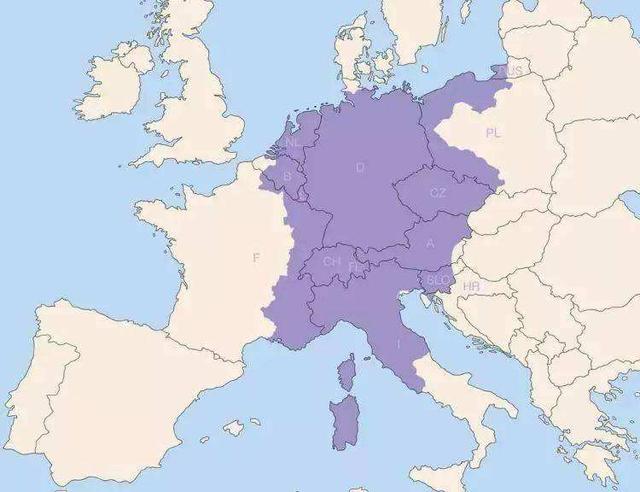今年1月份,鲍凤山在自家门前给乡亲们表演猴戏。 资料图片
探访新野猴戏:正牌“非遗”为何触了法律“红线”
□本报记者归欣张向阳鲍阿瞳
同情支持也好,质疑反对也罢,不管对猴戏持有何种态度,关心它的人都能注意到,猴戏的处境正在每况愈下。那么,猴戏在传承中,遇到了哪些困难?该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千年的猴戏,怎么耍下去?
共同的困境——
传人难寻,衣钵难托
猴戏所面临的较大危机,其实是许多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共同的困境——传人难寻,衣钵难托。
据新野县猴戏艺术协会统计,近年来,新野猴戏艺人已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万人,减少到目前的四五百人。
“这几年来,猴戏艺人的数量一直在下降。以前,有些村85%的人都耍猴,现在只剩下不到20%。”该县猕猴养殖艺术协会会长张俊然说。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还在坚守的新野猴戏艺人群体,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还活跃在外面的艺人,大多是45岁以上的,20多岁、30多岁的,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张俊然告诉记者。
当地的另一位猴戏“大腕”、新野猕猴养殖艺术协会发起人黄爱青证实了这种说法。“现在我一个月出五千,都招不来一个学生。”他一边感慨,一边回忆自己当年拜师的情景,“我师傅是我亲叔,就那,还摆了好几桌酒才答应,因为拜师的人太多了。”
他还告诉记者,就在一周前,一个20多岁的年轻“艺人”撂挑子不干了,到南方打工去了。
“时代变了,以前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身边的伙伴基本上都是干这个的。现在的年轻人,拨拨拣拣,周围有几个干这哩?”他说。
“后继乏人”,也许是形容新野猴戏传承的较准确词汇。当老艺人们渐渐老去,新艺人们不能或不愿接过衣钵,猴戏的没落和自然消亡,似乎已经顺理成章。
“照这样下去,不用谁来取缔,有一天猴戏自己就没了。”该县林业局退休老干部张成立说。
尴尬的现实——
地位不高,“钱”景不明
是因为挣钱不多,所以猴戏艺人越来越少了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全部。”省社科院民俗学者杨旭东博士说。
黄爱青也表示,优秀的猴戏艺人,收入也还过得去。他告诉记者,猴戏艺人以春节、麦收、秋收为时间节点,分成“三季”出去表演,干得好的话,一季能挣上万元。
杨旭东认为,猴戏之所以能从宫廷表演走向民间舞台,并传承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谋生功能。当这种功能凸显的时候,猴戏艺人自然就多;如果这功能有所削弱甚至消失,那猴戏艺人肯定越来越少,直至失传。
鲍湾村等地,人均不足一亩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猴戏是农民们较主要的副业。经过走访和调查,记者发现,如果以“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现在为时间坐标,新野猴戏带给当地艺人的存在感,恰似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猴戏的冰河时代,耍猴的道具被当做“四旧”毁掉,艺人挨斗,艺猴也难逃一劫,或被饿死,或被打杀;
改革开放初期,是猴戏的黄金时代,离开土地游走四方的艺人,有些因此挖到桶金,成为村里“较先富起来的人”;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致富的渠道越来越多,再加上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日益重视,“耍猴”渐渐被冷落,再次回到“墙角”。
在与一些老艺人的交谈中,记者发现,身份认同,或者说“面子”问题,是猴戏日益凋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古代,耍猴是被称为“下九流”的行当。而今天,也有不少人把它看成是利用猴子卖艺的“乞讨”行为。即使在鲍湾村等地,老乡们在谈起猴戏时也带着几分鄙夷,“说得好听是‘耍猴的’,说得难听就是‘要饭哩’。”
现如今,年轻人又能有几分耐心和定力去从事这份“掉价”的工作?黄爱青打了个比方:“过年了,几个同学聚一起,他说他在哪上学,他说他在哪打工,轮到你了,说是‘玩猴的’,说得出口吗?”
可能的出路——
主动改变,与时俱进
尽管猴戏处境堪忧,新野县文化部门、猴戏艺术协会、还活跃或已隐退的猴戏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把老辈人传下来的猴戏传承下去。用老艺人杨林贵的话说,“活得再卑贱,也不想让这老本行失传。”
但怎么传下去,显然是一个问题。像老辈人那样,“一根扁担两个箱,肩挑家当手牵猴”,走街串巷吆喝卖艺?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像传承人赵增举那样,找个景区栖身,继续坚守,好像也只是个例。世易时移,猴戏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
2014年,一对北漂夫妇傅帅帅、王熙创办了中华皮影艺术城,在传统皮影戏的基础上,加入了荧光、幻影、真人表演等元素,新编故事多对白少说唱,而且可以“私人订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同为“非遗”,皮影戏在创新后焕发了勃勃生机。新野猴戏,是否也能“与时俱进”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民俗学教授吴效群认为,“非遗是遗产,但不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很有必要,但较终应决定于市场。猴戏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主动创新。
“要想有人看,就要先改变。”黄爱青说。2002年,他和妻子逐渐退出外出表演的行列,专心在家驯养艺猴。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他的养殖场已有猕猴三百多只,并组建了一支8人的小型艺术团,跟省内许多景区都有合作,“长则半年,少则半月,演出时自带艺猴和道具。”黄爱青说,“目前运行得还不错。”
从单枪匹马的耍猴艺人,到带领一个集养殖、驯化、交易、承办演出于一身的艺术团体,黄爱青的“职业生涯”轨迹,似乎是猴戏的“升级版”,勾勒出新野猴戏“转型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能不能把猴戏组织起来,像马戏团那样?张俊然表示,协会有这个考虑,打算成立正规表演团,统一着装,给每一只艺猴上“户口”,让猴戏从街头走上舞台,更规范更文明。
对此,新野县文化部门也有一个比较切实的打算:计划在县城文化广场开辟一块演出场地,通过猴戏艺术协会,组织一些猴戏艺人公开表演猴戏,先从家乡人开始,提高猴戏的认同度和影响力。
记者手记
“高楼林立的城市,不应容不下一台猴戏。”在采访中,一位专家的话让记者印象深刻。
#p#分页标题#e#“非遗”是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这些记忆,不只有“高大上”的长城、故宫、大运河,也有“乡村范儿”的猴戏、皮影、捏泥人。正因为有了这些承载着我们五彩缤纷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大奇迹、小技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显得更加丰富、更加辉煌。
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总是让“濒危”、“抢救”这样的悲情字眼如影随形。关于猴戏的这场风波,不应仅停留在对猴戏生存的关注,更应引发人们的深度思考,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创新管理,为民间文化特别是“非遗”提供一个适宜的生存空间;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下,又如何为它们提供一方适宜的发展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