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为什么说约翰·达尔文可能将帝国历史的门槛提高了一个档次?
首先,通过统治实践和精英的象征性政治确保帝国一致性的理论,最终可以追溯到 S. N. Eisenstadt 的经典著作。
政治学家迈克尔·道尔 (Michael W. Doyle) 所著的《帝国》(Empires) (1986) 一书显示出惊人的长盛不衰,与其说是由于其并不总是很深刻的案例分析,不如说是因为帝国在政治上是“一种缺乏主权的主权”一个社区”。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对不同权力形式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脚注24在他的四部曲“社会权力的源泉”(1986-2013)中,不幸的是没有提出所希望的帝国理论并屈服于叙事的诱惑。
赫弗里德·明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的著作《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2005 年),它在几乎没有历史基础的情况下,从多伊尔(尤其是他的“奥古斯丁门槛”概念)和曼恩那里继承而来,主要准备了帝国与霸权之间的区别,并考察了地缘政治的行动模式。

尽管与蓬勃发展的新帝国史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充分考虑多帝国制度——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本书是在美国在单极时代后的岁月里假定美国无所不能的印象下写成的苏联集团和苏联的解体。
帝国分析的3个基准
如果要描述“牛津历史”进入的科学环境,就会出现关于衡量雄心勃勃的工作的可能标准的问题。这些标准体现在三部专著和两部百科全书中。
简·伯班克 (Jane Burbank) 和弗雷德里克·库珀 (Frederick Cooper) 的《世界历史上的帝国》(2010) 首先是一本缺乏证据且参考文献相对较少的教科书。是对自古以来帝王历史的介绍性概览。
专家不会在每个帝国的章节中发现任何新内容。现在,人们对 Jane Burbank(俄罗斯历史)和 Fred Cooper(非洲、西欧殖民历史)这样一个有成就的团队的期望不仅仅是一本教科书。. 伯班克和库珀用基本概念和论点丰富了帝国研究:帝国拥有权力库:“在特定历史情况下可以想象和可行的统治战略”。

它们的目的不是同质化,而是基于“合并和分化”的相互作用。这种差异在统治技术上很明显:“政体中的不同民族将受到不同的统治”。帝国是垂直组织的,但不是严格的等级制度,而是在不断的晋升和降级斗争中。
尽管它们以暴力为基础,但它们并不是纯粹的强制性制度,在这些制度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可以有明确的区分:“成功的帝国所产生的,通常是,既不是始终如一的忠诚,也不是始终如一的抵抗。
他们产生了临时住所”。如果帝国是成功的,即长寿的,那么它们的成功取决于灵活性和适应性。所有这些都是 Burbank 和 Cooper 将研究文献中的见解捆绑并浓缩成术语。
帝国程序史与范畴分析的融合,其水平在《牛津史》中几乎无人能及。值得注意的是,伯班克库珀通过谈论“相互交织的专横轨迹”故意避免对帝国历史进行明确的分期,这种相互依赖决不能被理解为计划中的网络形成,作为一个过分强调“全球”方面很高兴地建议。

伯班克和库珀对任何帝国道歉都不怀疑。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是矛盾的:1945 年之后的非殖民化并不是完全成功的,以“主权”为座右铭的一元论民族国家往往是一种幻想。
尽管权力傲慢无处不在,但更稳定的帝国善于管理——包括操纵——多样性。Burbank/Cooper 的最后一章,这里只是粗略地总结,是一篇精湛的浓缩文章,应该继续作为任何关于帝国过去的讨论的起点。
几年前,在牛津大学,约翰·达尔文可能将帝国历史的门槛提高了一个档次。
只有他以长期叙事的形式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叙事不能像简伯班克和弗雷德库珀的想法(或理论)积木那样轻易模仿或实验性地玩弄。达尔文被公认为大英帝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它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
在“帖木儿之后,自 1405 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他对 15 世纪的回归感到惊讶,甚至更多,因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早期章节是他整部优秀著作中最好的部分。达尔文实际上讲述了自欧洲分期的“中世纪晚期”以来帝国的连续历史。

他这样做是谨慎的,没有自负地标榜自己是世界历史学家。对现在的提及很清楚。历史的存在是为了让今天变得可以理解。比较史和关系史——经常被历史理论家宣称是对立的——悄悄地结合在一起,文化、社会和政治也是如此。
参考资料:
Bang, Peter Fibiger/Bayly, CA/Scheidel, Walter(编):牛津世界帝国史,2 卷,564 页/1,292 页,牛津 UP,牛津等。2021年
Pines、Yuri/Biran、Michal/Rüpke、Jörg(编):普遍规则的局限性。欧亚帝国比较,397 页,剑桥 UP,剑桥 2021。
最近一段时间,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被推上了企业家领袖的神坛,里面必然存在“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因素,很多经历国人难以模仿,但是马斯克推崇的所谓用“第一性原理”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是我们可以参考学习的;
“第一性原理”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在每一个系统的探索中,存在第一原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忽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这背后的思维方式就是“逻辑演绎法”,利用第一性原理找到系统之外的元前提,在此之上进行逻辑推导,产生必然结论;另一种我们更加熟悉的思维方式是“经验归纳法”,即我们经常说的“实践出真知”,很多书籍会把这两种思维方式上升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辩证对立,实际上,无论是马斯克利用第一原理拆解电动车/火箭来降低生产成本或是爱因斯坦的元起点“光速不变”原理,或多或少依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错误的经验也很宝贵;这里面有个例外,就是欧几里得,他用当时经验积累里完全不存在(甚至难以想象)的点、线、面概念加上逻辑推理,构成了几何学,周末去书店买了一本《几何原本》膜拜一下大神顺便重温一下初中几何知识。[捂脸]#马斯克蝉联世界首富#

●第一性原理思维(阅读录)
第一性原理,是人们的认知基本命题和假设,是公理,或是常识。
如:变化是永恒的;所有的人都会死。
第一性原理思维,就是从事件或问题的元起点出发,再作新的系统化思考,确定系统边界、要素、连接、功能或目标。不依赖原有的技术和经验,回归本体、本质、本性问题,重新在元起点、根基上的演绎思考,寻找或重新定义系统的第一性原理,思考新系统构建。
思考1:学习或建构新的模式,回归元起点,研究系统本质,打破原来经验模式,重塑成长型思维。系统的功能和目标是什么,系统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系统运行原理和逻辑模型是什么。现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如何从元起出发思考解决方案。
思考2: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老盯着别人怎么做,要回归本质去思考问题,别人做的不一定就是对的。特别是忌经验是从,限制我们的思维。盯着别人的做法,就不能友善看待自己的问题。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思考,易处于固定型思维模式。

思考3:不要老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要盯着竞争对手不放,因为巨人和对手很可能站错了地方。要回归本源,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确认站在哪里是对的。名人是优秀的,专家是高站位的,竞争对手是强大的,可自己呢?是拿来主义的引进思考,还努力去寻找第一性原理思维?
思考4:找到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培养第一性原理思思维,善于跨学科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的局限性,复杂问题往往涵盖多个学科。一个学科 知识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并且单一学科会限制你的思维方式。教育,就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涵盖教学法、管理学、认知学、心理学等。那如果这么说,是不是所有知识都要去学完呢,这是不可能的。如何进行跨学科学习呢?其实你只要掌握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即可。就像查理·芒格所倡导的,只学习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把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为基石模型,建立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和普世智慧。其实每门学科中真正的大道理并不算多,它们占了整个学科的95%的分量。进行跨学科学习,学习重要学科的重要思维模型,可以让我们多元思维武装自己的头脑。遇到复杂问题才能够从多个维度思考,才能找到第一性原理,才能通过公理化推导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思考5:教育的第一性原理:教育要以人为本;学习是自己的事,是主动的;学习是要学习的;学习的终极目标是成长型思维模式建构。而基于教育的第一原理思维,如办好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寻找、回归学校的理念(元起点),学校场景的建设和管理系统的构建(环境、条件、资源等),定位教育的愿景、使命、意义、目标。
隐含假设——万事万物的祛魅法则
李善友教授的《第一性原理》这本书通过先引入两个很基础的逻辑思维方式——归纳法与演绎法入手,得出演绎法比归纳法更真实的结论,并举以欧几里得的例子加以佐证。进而,他提出每个科学体系都是自洽的,而这个自洽的起点就是隐含假设。通过隐含假设以及演绎法的推理,构建出人类思想的大厦。欧几里得、 爱因斯坦、达尔文莫不如此。受到隐含假设的启发,渐渐地,我的重点不在于关注商业上如何破旧立新的问题,反而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隐含假设能够成就一个科学、思想体系,那么是否能够通过找到某种东西的源头,也就是这件事情的隐含假设,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分析世间万物的隐含假设,经济、政治、文化、崇拜等等隐含假设来破除迷雾,掀开迷雾背后的世界呢?我们能否通过隐含假设实现一种根本意义上的祛魅,最终实现整个思想体系的迭代更新呢?那么我们就从李善友教授这个最基本性的概念出发,试着破除一些固有的观念与成见,以期能够获得本真的第一源头。真相,是比所谓的社会真实更重要的东西。正如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发现问题,打破隐含假设的前提是要发现隐含假设。如何发现隐含假设?这里要解决一个“真”还是“假”的问题,那么这个过程的重要关键点就在于,要先从认知上打破固有思维。也就是要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存在即合理的。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 真的是真实的吗?隐含假设的启示使得我们去思考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文中有一幅图片,这张照片刊载于《巴黎竞赛》,画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装的黑人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乍一看来,这张照片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法兰西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而图中的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意味着法兰西帝国的子民们不分肤色,都效忠于它,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是如果去追溯一下这张照片以至于那个时代的隐含假设,我们就发现了矛盾之处:法兰西帝国是一个具有殖民和军事扩张意味的帝国,如果仅仅是“伟大的帝国”,是无法使黑人士兵心甘情愿地敬礼的。那么,这个隐含假设不就被推翻了吗?这个问题早就被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所研究,虽然他研究的时代还没有隐含假设的提出,但是万物同根,他的理论也可以完美契合隐含假设的理论。罗兰巴特认为,黑人士兵敬礼的被动性和被迫性在照片中被悄悄地隐藏起来了,其形象乃是一个实际的、天真的、无可争议的形象。显然,由于隐含假设的偷换,我们刚刚说的第二个意义被第一个意义所遮蔽、钝化了,似乎根本没有存在过。在这里,隐含假设相当于是一种神话,神话就是把事物钝化,使得变得单纯无害,给它们一个自然的和永恒的理由,给他们一种无需解释而只是事实陈述的明晰性。换句话说,隐含假设有一种使人不去探究某种事物“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作用,进而让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仅仅是看到这张照片的表意,而无法去仔细思考它为何会如此的原因。这就是隐含假设的生成路径。分析完这张图片,想必我们也对隐含假设背后的逻辑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隐含假设背后的神话功能使得我们在用眼睛去看某一事物的时候总是带着单纯的眼光的,实际上隐含了更加复杂的斗争内容。我想这种思维可以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追星。追星的隐含假设是什么呢?是我觉得这个人符合我心目中的某个形象,我愿意为ta的前途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狂热的追星族眼中,ta追的明星是那么符合自己内心的预期。可是如果我们用隐含假设地分析法进行分析的话,很快就会发现其矛盾之处,进而就会明白一个明星背后,是一支队伍,或许你所仰慕的明星看似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做出来的一个动作都是经过团队的悉心打磨而成的。隐含假设背后的神话原因是打造人设。如果破除掉这个隐含假设,回归到正常的隐含假设——明星也是人,也要赚钱。那么一切将迎刃而解,我们将实现明星团队给我们带来的神话,实现这个领域的祛魅,获得最本真的那个源头。以上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隐含假设也有可能是虚假的,问题就在于你要认出这个隐含假设,也即实现你固有思想的祛魅,并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寻找那个最最本真的隐含假设。这种思维如果推广到万事万物,必将实现我们思想上的重大飞跃。那么,你准备好打破一切重新来过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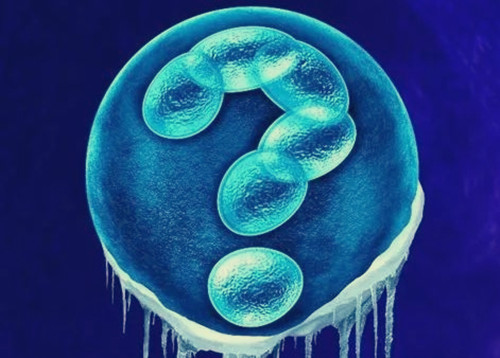
逻辑只能验证,不能保证正确。
逻辑推理必须有一个起点,从起点出发按逻辑的规则前进,得到结论。只要起点正确,逻辑规则运用无误,结论自然正确。
所以找到一个正确的起点非常重要。
起点可能是公理,即不言而喻正确的命题。但这样的命题其实非常难找,所以更多时候起点是假设。
如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就没有办法证明成立,所以后来有非欧几何。
万有引力也是假设,牛顿也不知道引力是什么?
社会科学更难找到公理,更多地要运用假设。所以逻辑正确不能保证结论正确,因为你可能一开始就错了。所以也不要以为逻辑万能。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常有惊人之语,事后却被打脸,不是他们不懂逻辑,而是经济学的假设只能并不符合现实或者只符合一部分,经过多步推导,看似逻辑严谨,实则越错越远。

#思考# #经济#
人类有两种主要的思维方式,一是归纳法,二是演绎法。归纳法是人们通过观察个别的现象,总结出普遍的规律,但是归纳法只能证伪,不能证明;演绎法是从一个基石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导得到新知识,但演绎法不能证伪,这个基石假设又称为元起点或第一性原理,就是任何系统中都有一个最根基的命题,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开创演绎思维之先河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欧几里得,他用公理化思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就是平直空间几何学,堪称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智慧。为什么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点线面及其关系,超越了感官对人类的禁闭,从已知可以推导出未知。这一思维的跳跃,导致了科学的诞生和现代科技的发明发展及创新,后来的笛卡尔,牛顿力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均受此影响。所有系统的元起点,受限于人类当前认知,现在依然未知,在西方是上帝,我们称之为道。另外,有一个技巧,就是如果想推翻一个结论,不要从结论下手,从他的隐含假设或者说是前提入手,这也是辩论高手常用的方法。平时和人辩论的时候,就可用这个方法,不要被对方的结论牵着鼻子走。

反映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以为主观会像镜子那样被动反映客观世界。这样的认识只能反映现象,而不能认识本质,完全不符合实际。认识只有是主动的,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本质最初正是与现象不符、超越现象的假设,再通过实证而成为规律。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若以反映而认识,他是根本不可能提出与一切经验相悖的相对时空观的假设。根本而言,要提出与现象相悖的假设,必然要求认识是主观主动、自主、决定,而这一主观假设是最终把握超越现象之规律的起点。
站在人的存在的起点上,分别和现实的逻辑是一切能被人理论的理论所必然依据的前提。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于先假设逻辑前提,然后根据逻辑规则推出结论,现实与理论因此错位。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了任何逻辑前提的唯一基础只能是现实,离开现实,没有任何逻辑前提有意义。现实的范畴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对现实关系剖析后的总体把握,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任何范畴都有着现实、生住坏灭的过程,同一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态,现实的秘密就藏在这些历史形态中。离开历史、具体、现实的范畴毫无意义。

幸甚!不咋探讨科学的中华文明开始探讨科学
清华教授赵南元(图1)和文化学者江晓原(图2)进行了一场有关科学的公开辩论,极具意义。江晓原认为:不正确的科学结论也是科学,例证是托勒密的地心说也促进人类发展。赵南元认为:用科学程序工作是科学家,但恰好是科学结果的正确性才证明科学家的伟大。
中国国内有一种科学宗教论:认为科学结论就是唯一正确,殊不知所有科学结论都可以被证伪,即所有科学结论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有限地成立。例如牛顿的三定律在低速世界是成立的,但到了光速世界就不成立了,这不能否定牛顿的伟大,但也说明牛顿的局限。
中国国内还有一种科学权威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认为资深、年纪大的院士们的科学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恰好相反,科学的起点是想象、假设,科学程序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论而已,所以年轻人才更有可能当科学家,发展新科学结论。例如爱因斯坦在20几岁发现相对论,50岁以后反而发现寥寥。

中国还有一种反权威论,例如本次争论的“反科学文化人”江晓原先生,他居然说不正确的科学结论也是科学。只要是科学结论在一定的时空内,科学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只不过会有新发现,证明该科学结论的局限性而已。
不论是把科学当宗教,还是把科学当权威,甚或是反权威,不甚探讨科学的中华文明开始大探讨、大辩论就是好事。新的百家争鸣,就是新的中华文明。
当我们在说一个事情「这不科学啊」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所说的「科学」是什么含义么?之前看过一个说法,科学至少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去把握。第一,就是数学的视角,以亚里士多德为起点。第二,就是物理的视角,以伽利略为起点。第三,就是历史的视角,以马克思为起点。数学是从假设和逻辑出发,实验是从现实验证出发,历史是从经验出发。三个维度又互相补充,三位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