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小档案206:新疆财经大学
姓名:新疆财经大学
出生日期:1950年
家庭情况:占地面积63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56.5万平方米
家庭成员:15个教学院部,42个本科专业;专任教师915人,
各类在读生21165人
现住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中路449号
身份证号码:10766
座右铭:经世济公、至善至诚
简历:
1950年,新疆省人民政府干部培训班成立
1959年,升格为新疆财经学院
1962年,转制为新疆财贸学校
1980年,恢复新疆财经学院建制
2000年,与新疆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新疆财政税务学校合并
2007年,更名为新疆财经大学
专业特长: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5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6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会计学、经济统计学、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国际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法学、新闻学、审计学、电子商务)

中共中央南方局高度关注地处国民党统治区腹地中心的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工作,当时全国内战已经爆发,根据党对四川农村工作的决议精神,要在全川建立5000个农村据点,重点放在川东各县,以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陈昌受命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负责人张黎群的安排,前往垫江建立据点,开展和平、民主运动。
垫江解放前属四川大竹专区第十行政区,地处华蓥山之东,与大竹后山、梁达虎南等游击根据地接壤,离重庆较近,又扼渝万咽喉,素有川东锁钥之称。早在30年代初,国民党对李光华同志领导的虎南特区实行军事围剿之后 ,就对垫江实行了严密的军事控制。垫江当时政局很复杂,反动派很注意垫江的风吹草动,除公开的“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外,敌探密布,如军垦处内潜伏着一个“川东特工组”,所以当时共产党在垫江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随时都有被抓坐牢杀头的危险。

1945年冬,陈昌带着助手兼妻子的何妨从岳池来到垫江,任务是潜伏下来,在农村建立据点,作社会调查,搜集情报,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直接关系,不发展党员,受特科直接领导。何妨,原名何送金,“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成员,1942年与陈昌相识,一直坚持与陈昌并肩作战。1945年经中央批准,成为陈昌第五任妻子。陈昌通过原在川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何凡昌介绍与新民乡黄寿伯认识,并通过黄的关系在新民中心校任教。
陈昌在学校结识了进步教师谭正品、肖文仲,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当时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终将破裂,应该建立一个农村据点,扎根于群众之中,才能应付时局的变化,为救国救民作出贡献,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农业合作社。1946年春,陈昌赴渝向张黎群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并请求给派助手。党组织即调派当作共产党员使用的蓝鸿恩到垫江协助陈昌工作。蓝到新民小学后,分担了陈昌担任的教员兼总务的职责。陈昌与肖文仲等人共同商定,决定在新民西山大通寺,以办合作农场的形式,建立农村据点。肖文仲原组织过“乐群敬业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性,由他出面筹集资金。经过数月精心准备,于1946年清明节前正式成立了新民乡农业合作社(当地农民惯称大通寺合作农场),陈昌任经理,肖文仲任社长,兰鸿恩任会计,何妨任出纳,委员有黄杰三、留美农学博士董时进、留美农学硕士董泽厚,并聘请了在重庆至诚银行任职的王志杰为顾问。董氏兄弟当时组织了一个农民党,创办刊物《现代农民》,发表过题为《论合作农场》的文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他们曾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农业顾问。陈昌为了掩护其革命活动,将“新民乡农业合作社”改称为“大通寺合作农场”。

大通寺合作农场地址选在西山大通寺(古庙,现属新民镇大通村),这里地处垫江、邻水、大竹三县交界的峰顶山(垫江最高山)山腰处,背靠大竹县后山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山高地瘠民穷,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革命活动。合作农场成立后,陈昌、蓝鸿恩、何妨、王立寿4人便常驻在农场。以大通寺为革命活动点,通过多种社会活动,搞调查研究,收集情报。
防火防盗防闺密之二
是否原谅闺蜜
今天一个陌生电话号码上午打了2次我没接,下午又打进来,我想打好几次了就接起来吧,我只喂了一声,那边哭声先传过来了,原来是那个被拉黑了的闺蜜,又弄个新号码。边哭边让我原谅她,信誓旦旦地说是我误解她了,她从来没有勾引我老公的想法,都三十年的朋友了,至诚地表白她是如何地珍惜看重我们之间的情宜,又说起我们刚相识时她如何地帮助我。

我俩是刚参加工作那年相识,同一年大学毕业,一起分到了当初那个小破企业,我分到车间与工人一起干活,她分到了厂机关搞质检,我性格懦弱,就连工人都欺负我,有什么事都找她倾诉,她性格泼辣敢说敢做,时间长了她就借着去车间检查产品的机会警告那些攀高踩低的人,还特意找到我们车间主任,让他多关照我,因为在下边车间r属于企业最基层最低层,不管是工人还是车间管理层都对机关人员格外高看一眼,她本身也是厂长身边的红人,不但长得漂亮还很会来事,每天早早地到单位帮厂长司机擦车丶收拾厂长办公室卫生丶给厂长沏茶倒水的,大家也很喜欢她,厂里把她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在她的关照下我在车间的日子好过多了。我后来提抜为车间技术员,她当上了质检科科长,同时配合搞工程预算。厂财务科是一女科长,居说与厂长关系不一般,工作第二年厂里效益挺好,财务科拟了一份奖金分配方案报到厂长那里,机关科室长以上的奖金比普通职员和车间人员多三倍,而我闺蜜作为科长,她的奖金却与我们下边一样少得可怜,她出出进进厂长办公室就看到了,找财务科长理论,财务科长说那个方案厂长已经批示同意了,并给出理由说闺蜜参加工作时间短,不可能与老人拿的一样多。我闺蜜可不吃这一套,威胁说若不把她的奖金提上来,就要上告到集团,后来这方案居然真给扰黄了,闺蜜是彻底地与财务科长结下了梁子。人们背后都议论说是闺密与厂长走得太近了,打翻了财务科长的醋坛子,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下马威,好戏还在后头呢。

第二年的四月份,闺蜜就被下放到了另一个车间当核算员。郁闷失落了很久,可能太苦闷了吧,也是对大好前途的无望,她竞然破罐子破摔了,与那个车间主任搞到了一起。
唉,先不说这些!今天她的诚心真挺打动我,想想我们也是共患难过的知己,我很感念在企业那几年她对我的仗义执言,心里真很矛盾是否该原谅她?
关于做人和做学问,《菜根谭》中说:“作人无甚高远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功夫,减除得物累,便超圣境。”
意即:“做人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不需要成就什么伟大的事业,只要能够摆脱世俗人情的干扰,就可跻身于名流;做学问没有诀窍和捷径,只要能够抵御名利的诱惑,保持宁静的心境,便可达到至高的境界。”
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却也真的很难。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卷入了物质丰富的世界,精神世界被冲击,被怀疑,变得摇摆不定。要想做个洒落的人,做至诚的学问,着实很难。

但还是有方法。
《菜根谭》告诉我们,做人不需要成就伟大的事业才算是名流,而是能够摆脱世俗人情的干扰,就算是名流。不媚俗,不卑躬屈膝,不阿谀奉承,不削尖了脑袋做事,不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做事洒脱磊落,对人以诚相待,宽厚处世,就能有名流之风。做学问,不被名利所左右,不患得患失,向着真理真知的方向探求,不被诱惑带偏,心中有星辰,胸中存大海,不求世俗的褒扬掌声,就能达到至高的境界。
难啊!难在哪儿?
比如我在头条写这篇短短的微头条,一方面是为了分享增益自身的心得,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博取网友的支持和鼓励,成为一个有成就感的创作者,我没有做到至纯至简。
如果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人可能会更容易接近纯粹的状态。但能达到财务自由的人,少之又少,尤其在消费型的社会形态下。

虽然尚未能到达,但心中已隐约看见那座风景,庄严秀丽,典雅高尚,只需努力前行,追寻和接近,就是很好的状态吧。
#菜根谭# #人生#
大医精诚,仁心仁术。
姚氏第三代~姚亦伟篇
55岁,未来可期
2016年的一天,姚亦伟走出上海眼科医院的大门,深深吸了一口气。这口呼吸里带着一种怅然,一种对接近自由的期许:未来的职业生涯会完全不同!也许是使命召唤,冥冥之中,跟随其祖父,亦然走上“民间医生”的路。
55岁,这个年纪对现代很多职业来说可算是“残花凋零”。但对于中医这个职业而言,却是一个正直盛年的好光景:经过历练之后的沉淀,经过沉淀之后的稳健,继而流露出在医术上的“随心所欲不逾矩”。
离开体制,离开平台,很多在职场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身边最多的声音是:姚亦伟自信过头了以他的成就来看,比他的祖父辈差远了……闻此言,姚亦伟一笑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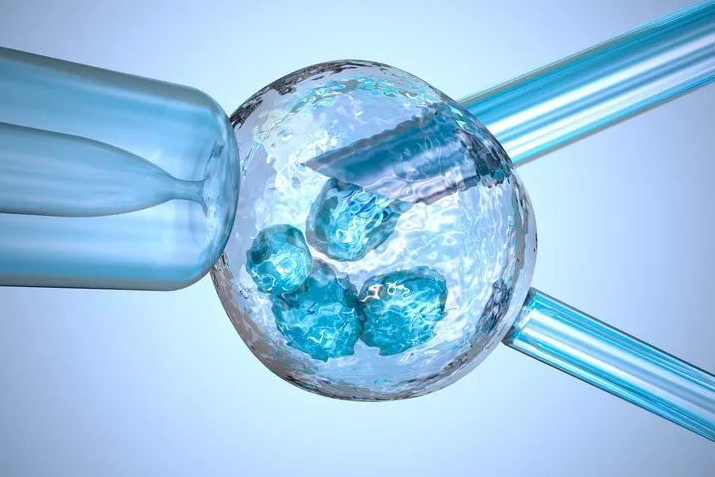
大医精诚
大学毕业后,姚亦伟随父侍方16年,期间父亲教他最多的是“为人处世”,传授最多的是”思想“。而秘方、处方之类却在其次。与父辈唯一不同的是,他性格不羁,做事绝不按部就班,喜欢天马行空。这又为将来在中医眼科的创新上具备与生俱来的优势。无论学习中国文化或中医,我们很难跳脱出前人的框架。总觉得自己所学浅薄,比不上先祖的十分之一,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尊师重道,含蓄内敛。而姚亦伟于此恰多了一份逍遥、自信。
为了更客观地了解姚亦伟的临床治疗,来到他的门诊。在一天的门诊中,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着一位医者如何为患者治病:在患者坐定之后,为其倒上一杯茶,姚亦伟先会观察一下患者,聊其近况。显然每位患者都不一样:职业、家庭背景、工作环境、性格、一直到症状……随后问起患者的症状有否改善以及身体的感觉如何,患者皆会把身体的感觉与姚亦伟描述一下:“喉咙有痰,早上起床有点痛、胃还是感觉不舒服、晚上嘴巴会发苦、近期睡眠不好、两只脚发冷、服药后眼睛感觉舒服很多,但停了就不行……不同患者的各种体感,在身体上,从上至下,从里至外,都会一一与姚亦伟叙述。之后是看舌苔,切脉。与患者沟通用药方案……期间还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穿插各种养生和健康的科普内容,甚至家长里短。当天的患者有跟随姚医师长达20多年的患者,也有第一次来门诊的;有大学退休教授、在职的企业财务,还有跟着父母就诊的中小学生。

这完全出乎对看病的常规印象。整个诊疗过程非常愉悦,患者敢于提出心中疑问,医生有问必答之外也会对患者提出很多问题。在一次门诊中即便身上有多处不适,不必挂3、4个科室的号,跑几栋楼几个楼层。这也许就是中医全身辩证的精华所在。如何在现代医疗上汲取这样的精华是我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姚亦伟在父辈的建树之上,自是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优势。在对于西医和中医的认知上,提出中药西治理论,充分利用好现代科技创造出的仪器,以确定眼疾的物理表现。而后用中医中药理论全身辩证,施以治疗,则可事半功倍。在临床上,也已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把西方医学科技用作中医药治疗的辅助方法。
姚氏三代的传承中,“慈悲为怀”四个字是姚亦伟体会最深的,也是在父辈的传承中始终贯穿的内容:想要成为一名“好医生”一定要有这四个字的修为。不然,即便医术再高明也只能是个二流医生。

作为一名医生,敢于承认对于某些病症依然束手无策,自己并不能看好所有的病,这便是一种至诚至信的态度。姚亦伟即是如此。对自己,对病人,都可做到问心无愧。一门学科是浩瀚无边的,但作为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如此才配得起“大医精诚”中的“诚”字。
行走在“民间”
戴老自喻“民间艺人”,这位画坛巨匠是怎样结识姚亦伟的?离开体制后,姚亦伟便自称“民间医生”。如此一联系,两位的莫逆之交的志同道合亦能体会一二。年逾八十,20副姚氏眼科的家族传承故事的画作,足足花了老先生大半年光景。在他笔下,画中姚氏三代中医传承历史的厚重感跃然纸上。
当戴老经人介绍找到姚亦伟时,一只眼睛已经失去光感,由于高血压,血管破损,已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戴老一生靠眼睛和双手创作,他余生只愿可以保住剩下那只眼睛的视力,为将来的创作留下“可能”。对此,姚亦伟义不容辞,答应全力为戴老的健康和视力保驾护航。6年来,戴老也经常和姚亦伟切磋“道法”,同时继续经典名著的创作。其实作画和行医又何尝不是同宗同源,所谓:大道归一,大道至简!
“很多人对中医的案例并不感兴趣,多带着嘲讽的意味,觉得中医“装神弄鬼”,即便在短时间内治愈疑难杂症,甚至治愈有些已经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这便更成为所谓“科学主义者”的笑谈。在我门诊治疗过的各类病例很多,多数是眼疾。然而中医是一个全身辩证的医学,病人的症状在眼部,要求医生从病人的全身辩证思考、施治。这是中医眼科和西医眼科最大的不同之处。然而,在门诊医治的各种病例都有:心血管疾病有之、皮肤病有之、免疫性疾病、癌症等亦有之,往往能起于沉疴。这就是中医全身辩证的伟大之处。
本文转自其他论坛 并非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