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阳洞林湖旁边有个实验中学,对面一条街全是小吃,米面炒菜,好不热闹。
我偶尔去那边办事,喜欢一家麻辣烫店,第一次吃的时候,买了个白吉馍,焦香酥脆,关键是年轻的老板娘笑靥如花,言语亲切。让人宾至如归。
周日和先生去,先生要吃米饭,我说不要,我就喜欢她这家。
先生坐了个位置,我去点餐,老板娘见我,说来啦?我说是。店里生意好的不得了。搞得老板娘不得不给我先生商量能否把我们的位置让给一堆学生,我们移步楼上的小位置,先生最乐于助人,说好啊。
这是个夫妻店,老板在厨房忙碌,进门的时候店主的女儿在外面,脖子上挂了个欢迎光临的牌子,有点小孩子玩趣的味道,却给店加分不少,老板妈妈负责送餐带收拾桌面。中午时分人来人往,勺盘叮当。
正吃饭间,见一幼小男孩,熟练拿抹布擦拭桌面,不禁大惊,小孩子长得双眼叠皮,一看就是个将来帅的主,拿抹布擦完桌子还知道拿手接着渣渣,再扔到垃圾桶。我问,你是店主的儿子吗?他点头。手上的工作一点都没停下,不一会就擦完了所有的桌子。先生打趣道:不要说话,影响孩子干活。

小店干的红红火火,生意是那一片最好的,店主应该挣了钱,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这个孩子更值钱。在幼小的年纪能吃苦,肯干活,帮助父母,这品德值多少钱?
无法用金钱衡量
荥阳真的是一座宝藏城市,有历史、有文化、有风景、有美食。衷心祝愿家乡发展越来越好。
石头丶豫中小老弟荥阳县志 —— “ 荥阳十景 ”
不从来就不在市级吃烩面,都是华而不实。是不是我们老百姓吃的东西,去中牟和荥阳吃的都是原汁原味的烩面都不超过十五块钱!想这些打着传统美食旗号的败类就该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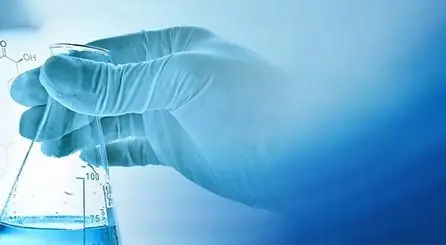
合记烩面是不是太贵了。
还是好这一口,培养两个小孩,也让他们品尝一下巩义的美食,回郭镇风味的米线。昨晚回来太晚还下雨,现在去荥阳,必须满足一下自己的念想。
说起河南烩面,不得不说郑州烩面,毕竟烩面在郑州要分好几个派系,有老式烩面,四厂咖喱烩面,萧记烩面,合记烩面,宴渠老烩面,白记烩面,这些在郑州数得着,唯独荥阳烩面和别的不一样,在荥阳见的最多的是加了卤味的烩面。#郑州头条#
就说在荥阳吃的这个8090烩面,大碗15元,小碗14元,中午一到12点就坐满了,烩面用的不是传统的白汤,出锅在烩面上边加了卤汤,牛肉是卤制的,烩面量大实惠,感觉有4片面,一碗就吃饱了。

这家店的特色就是价格实惠,份量足,8个人点了一份海带豆皮,水煮花生米,豆腐丝,凉拌牛肉,竟然没吃完,不仅烩面地道,小菜也很地道,你吃过这家烩面吗?在荥阳一大份15元,不算贵吧!#烩面# #美食# #郑州身边事#
【家乡美食之:煎饼(上)】
如果问起家乡人说一样家乡最具代表性的食物,正宗老乡百分之百会脱口而出煎饼。煎饼虽不是我爱吃的,但的确算是家乡的主食第一位的存在,嵌入所有的乡愁和回忆里,如果不做一记述实属缺憾。
查询一下,煎饼有据可考的历史能追溯到六千年前,河南荥阳曾经出土一件六千年前的陶鏊,经考证当是烙饼用的,后来出现的饼铛和摊煎饼用的鏊子即由此发展而来。六千年前就是中国煎饼的萌芽阶段。秦汉唐时期的所有的面食都被称为“饼”,这“饼”中,可能包括“煎饼”状的食品。”蒸饼”就是后世馒头,“汤饼”就是后世类面片、面条,“索饼”就是后世类面条。煎饼也是其中一种。魏晋墓南北朝、宋朝墓葬中多次出土过妇女用鏊煎饼的壁画,元、明、清三代,关于煎饼的记述更多。历史文献中如汉代《释名•释饮食》、明代《宋氏养生部》等书中亦多类似煎饼的“薄饼”的制法。最有名的是当推清代蒲松龄的《煎饼赋》“鏊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澎,乃随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蚁行,黄白忽变,斯须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热铛。一翻手而覆手,作十百而俄顷。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现在有人误以为煎饼起源于清代蒲松龄生活时期,实在是谬误。

从煎饼的历史来源与流行区域看,无疑是正宗的从事农耕种植的汉族劳动人民,几千年薪火相传而来。煎饼的制作也是融入无数位伟大母亲的血脉基因里了。
煎饼是一种流行区主要在北方,山东、山西和河北部分等地,其中山东较为广泛,主要流行在鲁南、鲁中、鲁西南,还有江苏与山东接壤的苏北一些乡镇。演员李幼斌主演的电视剧《闯关东》,真实再现了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长年累月跋山涉水在路上带什么吃的呢?如果是馒头、大饼之类的东西,放不了几天就坏了,就算是在冬天能多放几天,也是冻得像石头一样,啃不动,不适合带着上路。电视剧《闯关东》母子几人在渡海船上靠的就是吃煎饼保住性命。淮海战役中鲁南老百姓支前,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没有一点过分的溢美,而是实实在在的评价和赞扬。粟裕将军曾经深情地回忆山东解放区的群众:“临沂地区的人,宁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以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用小麦、玉米、小米、高粱做的煎饼送到部队”。其实何止战争时期,和平年代多少家乡打工人带着煎饼外出苦钱辛苦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多少学习啃着煎饼寒窗苦读进入高等学府。

烙煎饼的程序,说起来简单,是磨面、和面、支鏊子、烧火、摊面、烙煎饼,这些环节几千年没变,到我奶奶这一辈,也用石磨磨过面,小时候我也见过,大人一边转动石磨(也叫碾子),一边顺着石磨上的小孔加入泡好的小麦,也可以添加一些地瓜红薯、豆类等,磨好的面浆流到石磨下的瓦盆里。石磨磨面是重体力活,后来有电磨磨小麦面粉,用石磨基本看不到了。也有人加玉米面,口味偏甜。现在流行吃粗粮杂粮,就有专门制作杂粮煎饼的。
烙煎饼除了冬天极冷的时候,一般在院子里,主要因为是烧柴草烟火大,院子里好生火也好散烟。摊煎饼用的铁鏊子三根鏊子腿要垫高支好,这样下面合适有空间放柴火了。鏊子的历史几千年了,农耕时代用来摊面做合适,现在一些北方城市的炙子烤肉、铁板烧之类,也是鏊子的演变来的用法。这时候一般是奶奶负责烙煎饼,另外一人配合烧火,往往这个任务就派给我。烙煎饼有几样专用工具:刮子(竹子或者木制)、小铲子、油搭子(油搭子,粗布缝和而成,上面沾上点油,是防止面沾鏊子用的)。烧起来火,鏊子热的火候要掌握好,太热了煎饼容易糊,温度低则粘鏊子又不出活了。放面糊之前用油搭子擦擦鏊子,之后放上一勺子糊子,然后用刮子一左一右均匀把糊子摊匀,糊子很快就变干,用小铲子顺着在煎饼边上打开个口,用手揭开取下,放到盖垫上,一张煎饼就做成了。 烙煎饼快结束时候,奶奶会打几个鸡蛋和上葱花,鏊子上多擦点油,现做几个鸡蛋煎饼,被奶奶监督烧火的我,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与现在街头摊煎饼的手法不同,因为街头摊煎饼的鏊子小,一般是用小推子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转圈就可以了,家里鏊子大约七八十公分直径,单手转圈是转不过来的,烙出来的煎饼四五张就有一斤重。在家里烙煎饼,从摊面、赶面、铲煎饼要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如果现在有直播,一定会火爆。【文:屲屲仚冚,图片来源网络】
烙好的煎饼马上就变的很脆,这时候要稍微撒点水,然后对着几次成为比摊开杂志大小的形状,包上纱布,正常情况保存半个月没问题。烙煎饼是个体力话,六七口之家一次最少烙十几斤面,也只够家里十几天吃的。算下来,一年奶奶估计要烙二三十次几百斤煎饼,一辈子的辛劳可想而知。
河南荥阳,某乡镇举行庙会,除了附近的村民纷纷前往,还有很多游客专门驱车几十公里,到该乡镇参加庙会,但由于事先没有预留足够的停车位,导致很多车堵在门口。之后,有工作人员将游客的车辆,引导至附近麦地上,造成农作物受损。

据了解,这次庙会非常热闹,以雪游、大马戏、亲子新春游园、美食嘉年华等民俗文化为主,很受村民的喜欢,这也导致前来参加庙会的游人络绎不绝,交通拥堵。
从视频可以看到,麦地青悠悠的一片,充满了生机,可工作人员不断指引游客,将车辆停放到麦地上,造成部分麦苗受损。而在拍摄视频之前,已有数十辆车停在麦地上!
事发后,庙会举办方的工作人员透露,事情属实,但他们事先征得了当地村民的同意,后续将进行赔偿事宜。
目前,当地有关部门表示,他们后续将增派人手,妥善处理停车问题,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蚂蚁说法
1、对于麦地被车辆碾压破坏一事,网友的评论往一边倒。
“冬小麦不怕碾压,不要大惊小怪,返青时浇水施肥,长势会很好。”“吐槽麦地被压的,都是没下过地,没干过农活的人!”“在农村,麦苗旺长还要用石辊碾,抑制旺长促进分蘖,或者把牲畜赶到麦地啃苗。”“只要庙会方的赔偿到位,什么事情都好说!”

2、从法律上讲,只要村民同意,偶尔一次、两次将麦地用于停车,合法有效,但不能直接将麦地变成停车场。
事情发生后,有网友提出,庙会方将游客的车辆引导进麦地,是破坏公私财物。
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了,暂不讨论“麦子不怕压,压了长得更好”。单是事先征得了当地村民的同意,便不能以故意破坏公私财物定性。
但需注意的是,民法典第33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具体而言,村民享有的是土地承包权,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
也就是说,如果临时性停一下,没有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也没有对土地造成损害的,合法有效,但不能直接将麦地变成停车场,更不能改变土地的性质。

其次,如果庙会的组织者,事先经过农户同意,然后才将车引导停到麦田,双方可以就此事情进行协商解决,没有异议。
如果没有经过同意,擅自将车引导进入麦田,侵害了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对此,农户享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和消除影响等权利。
通俗地讲,就是如果没有经过农户的同意,不管有没有造成农田、麦苗的毁坏,农户都可以不让这些车辆停,并有向庙会组织者主张赔偿的权利。
最后,笔者认为,只要没有改变农田的性质,偶尔一次、两次,有关部门就不要反应过度了,也不要过度放大此事,否则过犹不及。
@蚂蚁说法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关注热点问题,从故事中学法律。
………………………………………………
头条热榜#律师来帮忙##我与宪法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