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1974年4月19日病逝后,昔日老部下,对其知之最深的陈长捷讲了一句话,说傅作义一辈子有个特点,“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这是他的本色,也是他厉害的地方。
陈长捷的这个说法很直白,但琢磨起来又很深奥,昔日华北王的“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究竟是怎样的呢?
咱们不妨来讲讲傅作义的一两件事,但其中的涵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问题。会上,傅作义提出,作为“华北剿总”总司令,他有权使用华北战斗序列的整个部队,但副总司令陈继承反对。
这个陈继承,是老蒋安插在华北的钉子,肩负着监视、掣肘傅作义的使命。当时,他不仅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而且还是北平警备总司令,同时还是华北的军统头子。
在会上,陈继承骄横跋扈地表示,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他,有的部队例如青年军师,只有他才能使用。除此之外,傅作义对直属部队的使用,他也有权过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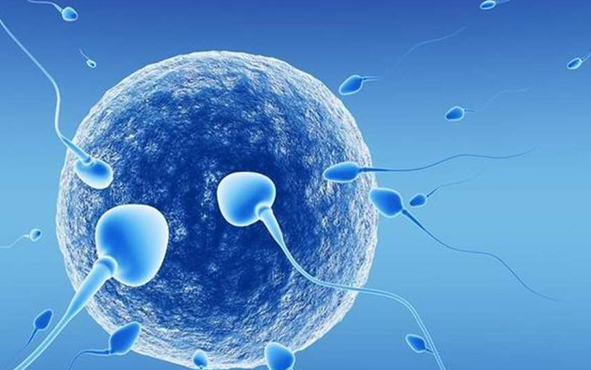
对于这个说法,傅作义当然不能接受,而陈继承仗着老蒋在背后支持,更不肯让步,于是在会场上,两人争吵起来,最后不欢而散。
咱们要看的是傅作义事后的做法。
从会场回来,傅作义气愤地对周围几个亲信人员说,想靠军统、中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苦百姓,我是不干的。
说完这话,第二天,傅作义便向老蒋坚决辞职,而且是一连三次给老蒋拍去了绵里藏针的电报。
在当时,傅作义的实力在华北明摆着,辞职便是他的“不说硬话”,而其中暗含的叫板,便是“不做软事”。
前两次,老蒋接到这样的电报,摆出姿态,好言相劝,竭力挽留。按照官场规矩,这时候傅作义就不应该第三次再发辞职电报了,但傅作义的目的没有达成,所以他继续表面软着来,实则硬着要。
老蒋接到第三封电报,想将傅作义一军,蒋说,你若能举荐一个如你一样的人才,可以接受辞呈。

这个时候,傅作义就不一样了。
他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句“软话”说得极有水平。
傅作义说,我认为陈继承可以。陈继承在华北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等各方面,完全可以胜任有余。
老蒋了解矛盾的激化是陈继承引起的,更能体会这是傅作义在用“软话”摊牌,思来想去,为风雨飘摇的大局计,最后不得不撤掉陈继承的职务,并允许傅作义举荐人选替代之。
傅作义不做软事,还有一点,一刀砍下去,那就必须见底。用这种“坚决”的态度,逼迫老蒋撤换了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职务后,傅作义并不罢手,之后他又连续撤掉了民政局长马汉三、社会局长温崇信,这两人一个是军统大特务,一个是中统大特务,都是不折不扣的坏东西。
接着朝下讲,更有意思。
1948年5、6月间,傅作义一连采取了诸多动作,例如成立河北省政府,将新闻处和民事处合并为政工处,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地盘。

这时候,老蒋为了抑制傅作义势头,又玩弄起奸雄伎俩。他向傅作义表示,可以给傅作义扩充四个军,并且给予番号。
傅作义头脑很清醒,知道老蒋不会平白无故扔馅饼。他对身边亲信说,又来这一套,你们记得1947年在张家口的教训吧,因为接受了扩编两个军的命令,我们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和一零四军被分别调往河北和东北。
身边亲信说,这是阴谋瓦解,我们必须强硬拒绝。
傅作义却说,强硬拒绝,我们理亏;欣然接受,我们受损。我看还是表面软,实质硬比较好。
傅作义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他没有拒绝老蒋,但老蒋给的四个军的番号,他做了巧妙处理,除把原保定绥署孙连仲留下的部队一个师和一个旅扩编为一一零军,荐举李世军为军长外,其余蒋所给的编制平均分给了所属各军,各增一个补充师。
这个做法,既有利于傅作义协调所指挥的中央军各军头的关系,避免老蒋疑心加重,又可防范以后老蒋以此为理由抽调、瓦解他的嫡系部队。
好一个软的手段,硬的结果。
1949年1月22日,北平城内20余万国民党军移师城外,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为此,毛主席曾当面夸赞傅作义:“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大历史的抉择时刻,傅作义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软事”。然而细细想来,那一时刻,不逆历史潮流,保下一座古城,避免生灵涂炭,又何尝不是一件了不起的“硬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