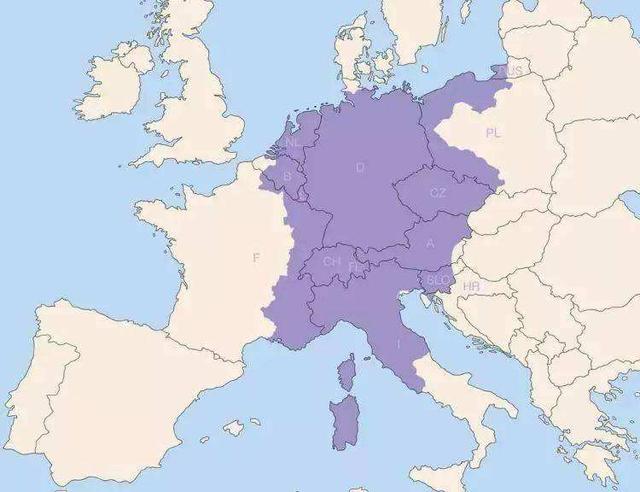刘邦大怒,将奏折摔下,高声道:“相国受商贾贿赂,为他人请上林苑地,还有王法吗!甚么游民无业?彼等既是游民,又怎能有心思开荒?”当下,便急召廷尉邹育入见。
邹育进了宫,揖过刘邦,不知又要处置甚么人,心中只是忐忑。
刘邦问道:“你斩了彭越,夜半可有彭王阴魂索命?”
邹育不知此话是何意,遂答道:“汉家天下,阳气冲天,岂有阴魂敢作祟?”
“那好,你既斩彭越,当是百鬼不侵了。今又有头等功臣触刑律,着你立即拿下。”
“是何人斗胆?”
“萧相国受贿,着你将他拿下,械系入狱,听候处置。”
邹育当即面如土色,口齿结巴:“这,这……这如何使得?”
刘邦便高声叱道:“彭王无辜,你尚且能问出罪来,相国如何就动不得?”
邹育闻刘邦提起彭王事,心中一凛,又不敢反驳,只得辩解道:“那相国,乃百官之首也。按汉律,以下犯上乃逆伦,故下官不敢纠弹相国。”

“恐不是你怕以下犯上吧?朝中文官,皆以攀附相国而自固,上下勾结,连我的话也不大听了。”
邹育慌忙伏地,请罪道:“陛下令出如山,微臣怎敢违拗?既有诏,臣这便去相国府拿人,然需赐臣符节,也好持节捕人,否则便是造反了。”
“你造反,也强于相国造反!今日他敢受贿,我死后,他就定要造反了。我赐你符节,你尽管去,只拿相国一人,不得惊扰他眷属。”
邹育这才松了口气,领了符节退下。待安排妥帖,即率廷尉府吏员百余人,浩浩荡荡开往相府。
那相府萧逢时出门来看,但见兵卒林立,街上无一闲散行人,还当是皇帝即将驾临,连忙奔告萧何。
萧何正在书房闭目养神,闻报,微微一笑:“陛下岂能来相府?你只管守住门,非陛下,天王老子亦不许进。”
少顷,邹育下得车来,望了一眼门楣,撩衣便要进。萧逢时识得邹育,情知有异,挺身挡在了门前,赔笑道:“小臣为相府长史萧逢时。邹公有何事?容我通报。”

“奉上谕,面见相国。”
“上谕何在?可否出示?”
那邹育并非沛县旧部,与萧逢时并不熟,只道:“我奉上命,会办公事。无须长史你通报,请借过。”
那萧逢时资历甚深,远胜于灌婴、王陵等辈,哪里将一个新任廷尉放在眼里?闻听此言,不由火起,断然道:“此地为相国府,不经通报,百官皆不得入。”
邹育便将符节一举:“奉上命,何人敢阻?”
萧逢时见是错金龙符,知道来头不小,心中便暗自叫苦,却仍是嘴硬道:“廷尉一人请入内,其余人等,可在廊下等候。”
邹育不禁大怒:“一个长史,敢阻九卿乎?来人,与我拿下!”
左右吏员闻命,一拥而上,将萧逢时按倒在地,一把绳索捆了。相府内属吏见了,不由大惊,都掣出剑来,一齐冲出大门,将邹育等一众官差逼住。
邹育怒喝道:“阻拦公务,是要造反吗?”

众相府属吏登时大哗:“擅闯相府,尔等才是造反!”
那些警戒的禁军见了,亦满面惊惶,不知该助哪一边,只是呆立观望。
正僵持间,萧何闻声出来,对属员喝道:“不得放肆!”又向邹育一揖,“不知邹公驾临,恕老臣失礼。”
那邹育已知相国府厉害,也无心周旋,当即口传上谕:“奉上谕:相国干犯禁令,收了商贾之贿,着提至廷尉府问话。”
萧何闻言,脸色一变,忽想起查抄淮阴侯府情景,将头一昂,问道:“可要抄家?”
邹育连忙道:“哪里?相国多虑了。有令,仅提相国一人,无涉眷属。臣下职分在身,有所冒犯,万望宽恕。”说罢,向后一使眼色,众属吏就要上前拿人。
萧何冷冷一笑:“且慢!廷尉府是何衙门?”
邹育道:“奉上命执法。”
“既然执法,可知汉律?我乃汉家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罪过,请御史台先行弹劾,罢职后,才轮到你廷尉府拿人。你那些爪牙,请闪避,我随你去就是了。”

邹育正要称谢,忽闻萧何又道:“将我那长史放开!彼为沛县人,君上也不敢如此待他。”
邹育也知萧府之人绝非寻常,这面子定然要给,于是一笑:“好说,放人!请相国上车。”
一行人遂押着萧何,转了几条街,来至诏狱。萧何望见诏狱大门,便微微吃惊:“邹公,来此处何干?”
邹育也不答话,跳下车来,一声断喝:“来人,将罪臣萧何拿下,枷锁伺候!”
众公差立时扑上来,褫去萧何衣冠,将一个二十斤重的枷,套在萧何头上,又将锁链缚住双腿。
萧何也不挣扎,只仰首叹道:“我今日便是商鞅了,作法而自毙!只不知,堂堂汉律何在?”
邹育适才受了萧逢时顶撞,也正气闷,便道:“相国今日才知汉律?若早知汉律,为何要强买民田?”
“为买田事,何至于下狱?”
“相国,非为下狱也,且械系于此,听候处分。吃喝用度,尽管令家臣送来,本衙决不刁难。”说罢,便唤来狱令,教他调来两个犯官,与萧何同室,以便伺候。
狱令此生,从未见过如许高官入狱,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便将萧何当作了死刑犯。
一连关了数日,并无人来提审。那狱令每日来巡视,颐指气使。因平日威风惯了,也将萧何叱来喝去。
萧何左思右想,只觉得如同梦寐:二十年勤谨奉公,竟落得形同死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