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三年服役期满后没能提干,办好退伍证,领了117元退伍费和50斤全国粮票。刚坐上从商丘到洛阳的火车,一辆军用吉普直接冲上站台,只见一名军人连声地喊“阎连科在哪”
1958年,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家中兄妹四人,他是老幺,本应是父母最疼爱的一个,但因为家中贫穷,从未有过什么特殊待遇。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父母甚至连他的出生日期都没记住。
直到1978年,20岁的阎连科报名参军填写登记表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出生日期必须要填写。”爹娘回忆了半天“那会刚立秋,天还热着呢!就写8月24日吧!”至此,阎连科的出生日期才最终被确定下来。
来到部队后的阎连科一心想提干穿四个兜的军装,但他的军事训练成绩只能勉强及格,他一度认为自己提干无望。但新兵下连前的实弹射击,他打了98环,因此荣立三等功,他又重新燃起提干的希望之火。

等连时,他又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教导员推荐去了写作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教导员又把他安排在了营部报道员的岗位上。
那时部队缺乏“笔杆子”,规定“在省级报刊上发表3篇文章,记嘉奖一次;发表五篇文章,记三等功一次。”
此时的阎连科已经有了一个三等功,如果再立一个三等功,提干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开始在每个连队挖掘素材,写成文章到处投稿。最终在当兵第三年时完成任务,再次荣立三等功。
正当他喜滋滋地以为自己就此能提干时,一纸文件下来粉碎了他的提干梦。
原来对越自卫反击战刚结束,立功提干的战士太多,为了限制军官的数量,上级下发了“未经军校培训的战士不得提干”的文件。阎连科已经过了考军校的年龄,且三年服役期已满,绝望之下,阎连科办好退伍证,手拿117元退伍费和50斤全国通用粮票,坐上了从商丘到洛阳的火车。

火车即将启动时,一辆军用吉普突然冲上站台,一名军人打开车窗,一连声地喊“阎连科,阎连科在哪个车厢?”
阎连科心里一惊,忐忑不安地下了火车朝吉普车跑去......
原来喊他的人是团长,他告诉阎连科“你给武汉军区编的独幕剧在全军文艺汇演上拿了一等奖,为了保留战士中的文艺骨干,总政特批了20个提干名额,我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指标。”
阎连科有些犹豫,因为他父亲的身体不好,家中缺少劳力,团长见状说道“要不这样,你先回家考虑七天。七天后,如果你不回来,这个指标就作废。”
阎连科感激地看了团长一眼,再次登上火车回了老家。
七天后,阎连科返回部队,没多久就换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四个兜军装,成为一名正排级军官。然而,他思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仕途,选择追求自己的写作梦想。
8年后,阎连科考上了军艺文学系,成了莫言、李存葆等大作家的师弟。毕业后,他留在了二炮电视艺术中心做编辑。在此期间,他边工作边创作边投稿。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是以军中主旋律为主,没有太多自己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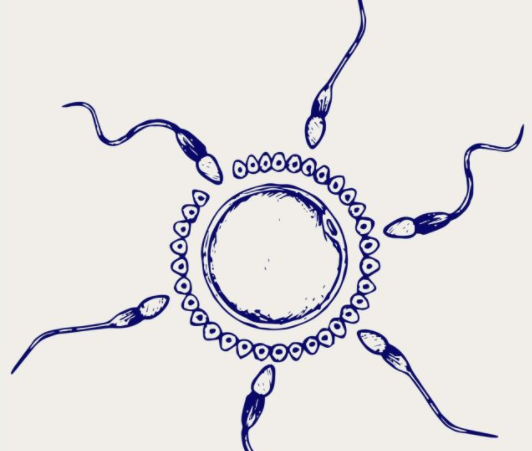
但阎连科对写作有着谜一样的执著,每次写作只要铺开稿纸,他就如老僧入定一般,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嘈杂,他都能照写不误。
直到1995年,有出版社主动提出给阎连科出版全部作品的文集。他借机重新整理了一遍自己的作品,发现自己写了几十个中篇,讲得大体是同一个故事;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可这些人物大同小异,几乎也就是一个人物。他觉得这是在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时间。
恰巧的是,这一年他因为严重的腰椎和颈椎病导致创作速度慢了下来。他就这样一边反省、一边写作,艰难地完成了多部与以往风格迥异的作品。
2003年,他的《受活》发表,当即引来一片质疑之声。他也因此脱下穿了26年的军装,转业到了北京作协。
没了束缚后,阎连科创作更加大胆,先后完成了《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自创了“神实主义”,被国内读者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然而老家的一个堂叔去世,阎连科赶回老家奔丧,一个堂妹问他“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啥不写写咱家的事呢?”
这句话让阎连科有些无地自容,他看着承载了父辈们的艰辛与希望的这片土地,想起自己的逃离,一种无法言喻的滋味涌上心头。
回到北京后,阎连科一改自己“魔幻现实”风格,用极为平和的叙事方式创作出《我与父辈》。
《我与父辈》成稿时,帮他整理成电子版的几个学生哭着说“阎老师,看完这本《我与父辈》,才感受到父母的伟大。”
后来《我与父辈》在上海复旦召开初版会,一名高中女生说“我是独生女,以前只知道索取,从不与父母沟通,也不理解他们对我的爱。读完《我与父辈》后,我哭了,开始尝试与父母交流,开始试着理解他们。”
这名女生买了两本《我与父辈》,一本送给父母,一本留给自己。

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我与父辈》是一个儿子跪在父母坟前的忏悔,也是一本经历过的人读完后会产生同感,没经历过的人读完后会产生警醒的书。
而读者却说,《我与父辈》是一本父母看完后想送给子女的书,请了解你们的父辈;也是一本子女读完后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
我与父辈蚀骨情深
当兵第四年,24岁的阎连科因为一幕话剧而意外提干。有个和他同样出身农村的战友说“你现在是军官,得找个能在事业上帮你的媳妇。”随后给他介绍了一位军官女护士。
阎连科当兵最初的想法是“走出农村”,这源于他对贫穷的农村有着深刻的体会。但初入军营,他发现自己的体能不太跟得上定下的“提干”目标。沮丧之时,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因为视力好,新兵下连前的实弹射击考核中,他用10发子弹打了100环。正在现场观摩的团首长不太相信一个新兵能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当即又给了他10发子弹,阎连科这次打了98环。

恰巧师里要组织新兵进行实弹射击比赛,团首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让你代表新兵参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
“保证完成任务”阎连科惊喜地回答。
就是在这场射击比赛中,阎连科再次打了98环,连队给他报请了三等功。一时间,阎连科成了有名的“神射手”,这让他觉得自己离提干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然而还没等到下连,对越自卫反击战就爆发了,当时前线部队要从各大军区抽调战斗骨干,阎连科作为“神射手”几乎铁定要被抽走。但教导员得知阎连科是高中生,且负责部队的文书和板报后,就把他派到了武汉军区一个创作班学习。
从学习班归来后,阎连科留在营部当了报道员,依旧负责文书和板报。正是在这个岗位上,阎连科得知“在省级报刊上发表5篇文章可记三等功一次”。于是,他开始收集各个连队的趣闻轶事,自己进行艺术加工后投稿。

当兵第三年时,阎连科总算完成发表5篇文章的任务,再次荣立三等功。原本以为就此能提干的他,此时却接到如同晴天霹雳的文件。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许多从前线返回的战士都因功提干,一下子多了许多军官,但却无处安排,于是各军区下发了“未经军校培训的战士不得提干”的文件,阎连科刚好卡在这个时间点上。
提干无望,阎连科办好退伍证,领了退伍费登上了返乡的列车。没想到列车即将开动时,团长直接把他喊下来说“你提干了。”
原来阎连科为武汉军区编的一幕话剧《二挂鞭》在全军文艺汇演上获得了一等奖,军区首长特批了二十个提干名额,团长为阎连科争取到了一个。
提干没多久后,一个和他同样出身的战友说“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得找个有城镇户口的姑娘结婚,对你的事业有帮助。”
阎连科深以为然,便同意了战友给他介绍对象。没想到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官二代,女方的父亲是某县武装部长的女儿,还在军校读书,毕业后就是军官护士。在战友的鼓励下,阎连科试着给女方写了一封信,女方回信很快,阎连科觉得这事有戏,又写了一封深情满满的情书寄过去,没想到女方很久都没回信。

恰巧阎连科刚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战友买来这本杂志寄给了姑娘,姑娘这次回信很快,但内容只有一句话“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
这句话让阎连科意识到自己即便成了军官,也改变不了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于是他放弃仕途,报考了军艺文学系。
从军艺毕业后,阎连科留在了二炮电视艺术中心成为一名专职编辑,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事业。
这期间,阎连科的作品以军中主旋律为主,虽然发表的作品不少,但在文坛上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直到2003年,他的《受活》发表,轰动文坛,获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然而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阎连科脱下穿了26年的军装。
没有了特殊身份的束缚,阎连科创作风格逐渐转变,自创了“神实主义”,如《丁庄梦》、《风雅颂》和《炸裂志》等作品,也因此被读者冠以“中国荒诞主义大师”的称号。

直到有一天,他的本家堂叔去世,阎连科赶回河南老家奔丧。在灵棚里,一个堂妹问他“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啥不写写咱家的事情呢?”
堂妹的无心之语触动了阎连科,让他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辈们和当兵之前的故乡。
回到北京后,阎连科把自己关在书房,以老家田湖为背景 ,以父辈为主角,创作出了《我与父辈》。
阎连科把《我与父辈》的书稿交给打印室整理成电子版,当他取书稿时,几个女打字员哭着说“阎老师,我们打了那么多小说,只有这一本是边哭边整理的。”
电子版发到儿子的邮箱,几天后儿子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看完了,哭了。”
《我与父辈》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的初版会上,复旦的一名副校长和阎连科是同龄人,他强烈要求阎连科在复旦也举行一场交流会,因为这名副校长觉得“很有必要让现在的孩子知道父辈的不易。”

在复旦附中的交流会上,一名高一女生说“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可父母还是不停地向我施加压力,这让我很难接受,也无法理解他们。但我读完《我与父辈》后,才理解了父母的不易,开始学会与他们沟通交流。”
这名女生买了两本《我与父辈》,一本留给自己,一本送给父母。
《我与父辈》是一本没经历过的人会产生启迪,经历过的人会产生警醒的书,也是一本父母读完想送给儿女的书: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更是一本儿女读完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
当兵第三年,阎连科因为写作立了第二个三等功,但因为政策变化,提干失败。办好退伍证拿着110元退伍费刚登上回家的火车,团长开着吉普直接冲进站台对他说“你提干了。”
1978年底,阎连科通过体检政审,成为了一名军人。这在当时的农村,是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重大转折。所以阎连科来到新兵连后非常努力,可惜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十分出色,单杠、双杠、长跑,对他来说不是容易对付的事情。

但阎连科的视力特别好,射击训练又特别认真,等到实弹考核时,他用10发子弹打了100环。团长听说后表示不信一个刚入伍两个多月的新兵能打出这么好的成绩,把他单独叫出来,又发给了他10发子弹,这次阎连科打了99环。团长当场拍板让阎连科代表新兵参加师里组织的实弹射击比赛。
这次比赛,阎连科打了98环,与另一个其他团的新兵并列第三名。回到团里后,领导为了表彰阎连科,给他报请了三等功。
“两个三等功就能提干,你就差一个了”这是老兵告诉阎连科的原话。可第一个三等功有运气的成分,想立第二个三等功可就太难了。
好在那时部队特别注重文化宣传,阎连科作为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一,本就写得一手漂亮的新魏体,再加上教导员惜才爱才,下连时就把他调到了营部当通讯员。
通讯员的工作并不复杂,每日除了收发文件,剩下的个人时间很多。阎连科本就喜欢写写画画,再加上有“提干穿四个兜军装”的想法加持,于是他经常写一些报道投稿。还真别说,投出去的稿子被采用后不但有稿费,还一点一点地增加了他的知名度。等到当兵第二年时,阎连科已经是团里有名的“小作家”, 多次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再一次荣立三等功。

两个三等功已经满足提干的条件,阎连科以为自己这次稳了,没想到上级突然下来文件“未经军校培训的战士不得直接提干”。“提干穿四个兜军装”的梦想就此搁浅,恰巧老家村支书来信“你是高中生,又当过兵入了党,不如回来当村干部吧!”
自知提干无望的阎连科办了退伍证,领到了110块退伍费和50斤全国通用粮票,用赚来的稿费给家人买了些糖和土特产,头也不回的去了火车站。
刚登上火车没多久,一辆军用吉普车直接开上站台,坐在副驾驶的军人一连声地喊“阎连科在哪?”
阎连科听到有人喊自己,打眼一看是团长,急忙从车厢下来,团长拉着他的胳膊“你提干了。”
原来阎连科为武汉军区编的一幕话剧在北京全军汇演上拿了一等奖,军区政治部主任当场特批了20个提干名额,阎连科排在第一个。
团长告诉他“既然你已经上了火车,那就先回去吧,给你七天的时间考虑。七天后如果不回来,这个名额就作废了。”

阎连科最终还是选择了提干,母亲为了帮他凑齐花掉的退伍费,还把家里的猪卖了。但提干后的阎连科并未走仕途,而是选择走自己的文学梦想。为此,他放弃了师宣传科科长的位子,转而考上了军艺文学系。
在阎连科之前,军艺文学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如莫言、李存葆等。看到他们红得发紫,阎连科立下了用手中的笔实现心中抱负的目标。
从军艺毕业后,阎连科分到了二炮电视中心成为一名编剧。在这段时期,他的作品都是军中主旋律报道为主。直到1996年,他发表的《黄金洞》获得鲁迅文学奖。1997年,中篇小说《年月日》发表,开始引起文坛关注。在随后的几年里,阎连科的作品呈爆发式增长,各类奖项拿到手软。
然而2003年的一部小说《受活》意外地让他脱下穿了26年的军装,就连老家的县长也打来电话说“连科,你其实是咱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想到自己自小离家,想到父辈的艰辛,想到那片难舍难分的故土。原本以为成名以后是家乡的骄傲,没想到却成了家乡最不受欢迎的人。
多年后,阎连科的一个叔叔去世,他赶回老家奔丧。在守灵的灵棚里,一个堂妹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怎么不写一写咱家的事呢?”
这句话对阎连科的触动很大,他发现自己依赖的故乡正在发生变化,父辈们留下的痕迹正在消失。于是,他一改昔日神实主义风格,以老家为蓝图,以父辈为主角,用朴素的文字写出了《我与父辈》。
《我与父辈》成稿时,阎连科拿给打印社整理,整理完以后去拿稿子,一个打字员流着泪说:阎老师,这部书我是哭着看完的。
电子版发到儿子的邮箱,儿子给他发了条信息“哭着看完的”。
《我与父辈》初版会上,上海交大附中一个16岁女生说“我以前从来不会和父母沟通,也不理解他们的艰辛,读完《我与父辈》后,我才知道父母的不易,也学会了如何与他们交流。”

这个女生买了两本《我与父辈》,一本送给父母,一本送给最好的同学。
有读者说《我与父辈》是一种经历过的人会产生共鸣,没经历过的人会产生警醒的书。也有读者看完《我与父辈》后送给父母,感恩我们的父辈;送给子女,请主动了解你们的父辈。
点击下方链接或看一看即可!
你知道莫言是怎么参军怎么提干的吗
莫言是1976年以21岁大龄参军的,1982年提干的,而且是破格提干的。为什么要破格提干呢?你跟着我往下看。莫言1955年出生,小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然后放牛,劳动。1973年,莫言18岁,莫言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在五叔的介绍下,莫言进了加工厂当了合同工。当时莫言写得一手好字,被领导发现,便让他办厂里的黑板报,每期的黑板报图文并茂,厂里上下都说办的不错。后来厂里办工人夜校,经大家推荐,小学五年级的莫言,给厂里一群初中毕业的教语文。莫言想参军,连续三年在村里报名,都因为中农成分被刷了下来。1976年,莫言21岁,也是最后一年参军机会,他在棉花加工厂报名参军,他的工友是 公社武装部长儿子,这个工友也向父亲推荐说,莫言在厂子里表现很好。就这样,莫言参了军。村里的个别人对此有看法,认为应该优先贫下中农。民兵队长给他送通知书,远远地扔给他,头也不回走了。到了新兵连,莫言因为文笔好,做为新兵代表上台发言。这是个非常露脸机会,做好了会给首长留好印象,对前途很有利。但是莫言弄砸了。他上台发言时,台上有空椅子,他以为可以坐,就坐下发言。但那是给首长坐的,他应该站着发言。发言完,班长告诉他,那椅子是给首长准备的。班长还说,你前途完了。莫言立刻大哭,自己来当兵就是为了进步,这刚参军就弄这事。莫言写了沉痛检查,央求班长送上去。就在莫言心情崩溃的这段时间里,又受到一次致命打击。新兵连指导员给了他一封信要他看。莫言看后,一身冷汗,这是村里来的一封举报信,说莫言出身不好,不能参军。莫言哭着对指导员说,你千万别让我回去,回去我就完蛋了。指导员说,我把你叫来,是让你知道这件事,就是让你珍惜机会,加倍好好干。莫言经过这两件事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当上了副班长。后来因为莫言材料写的好,被调到教导队当教员,这是提干的节奏了。但是,莫言再次遭受挫折,他虽然是个7年军龄的老兵,但还是一个没有干部编制的教员。而且当时规定,超过24周岁的战士不再提干,而他参军的时候就21岁了。到1982年的时候已经27岁。也就是说,按照规定,提干无望了,难道还得复员回村里吗?莫言真的绝望了。但是,莫言的命运还是发生了转折。1981年5月,莫言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在保定《莲池》杂志上,此刻,莫言激动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拿到稿费那一刻,买了一瓶刘伶醉,四只烧鸡,叫来战友,一醉方休。莫言突出的才能,引起了上级注意,上级主管思想工作的领导,偷偷去听了莫言讲的一堂课。听完以后,认为莫言这样的人这么有才,不提干太可惜了。这位领导亲自带着莫言发表的文章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提拔莫言。上级领导思想很灵活,看了莫言文章后欣然同意提干。就这样,在1982年那个炎热的夏季,莫言成为一名排级干部。莫言这次的鲤鱼跳龙门,整整用了七年,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只有他自己知道。后来莫言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是破格录取。当他知道招生的消息时,报名已经结束。他就把刊有小说《民间音乐》杂志拿给文学系主任徐怀中看,还有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的二百字左右点评,徐主任看了后,说,这个人即使文化考试不及格,也要破格录取他。后来徐主任告诉莫言,他的专业课打了满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1986年,莫言发表了著名的小说《红高粱》,还被张艺谋改变为电影,从而红遍全国。可以看出,莫言年轻时经历了很多磨难,但他都是靠他的才干一步步走了过来,最后获得了成功。#莫言# #热点# #人生# #社会# #人生百态# #故事#

我不是想蹭李少莉美女局长的热度,真的不是,只是想问问那些骂她的人:你们好意思吗?
根据我几天的观察,骂她的人,主要有这么三种——
第一种:就是想要李局长“赏”钱的。
这些想在头条上发财的人,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从各个角度骂李局长,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人们的眼球。
他们在网上兴风作浪,制造舆情热度。
他们一煽风点火,围观的人们就如过江之鲫蜂拥而至。他们的展现量呀阅读量呀就唰唰唰地上涨啦。这两个量互为推手,你追我赶:你量大了,我也要大。于是啊,这两个量,就变成了红红绿绿的美丽钞票。
第二种,就是没有李局长漂亮的女人。
这些女人,本身就长得不怎么样,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的逝去,容颜的衰老,她们已经对自己很不满意了。
再加上老公的冷嘲热讽,心里可能时时窝着一肚子火,没有发泄处。

李局长出来了,显得这么年轻靓丽,穿戴又这么高雅大方美观。一对比,自己就成了陪衬人啦,越发“不堪入目”。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骂。
第三种,是那些参加工作多年,因为没有成绩,所以没有提干的人。
有些人,自己干工作就是为了拿钱。本来,为了拿钱而工作,也是对的,不必非议妄议。但是这些人,他们干工作不用心,不热心,很随心,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这样下来,工作没有成绩,也没有什么人缘,晋级提干,自然无望。因为自己晋不了级,提不了干,就对那些晋级提干者羡慕嫉妒恨。特别是对像李局长这样一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的漂亮女人,他们更是羡慕嫉妒恨到牙齿发痒眼睛红,不骂她,骂谁?
第四种,政治敏感,看风使舵的人。
这种人,看见国家号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就开始过度解读,甚至故意曲解。国家的号召是对的,英明的,是约束所有的财政人员,特别是手中有权的人,不能慷国家之慨,胡乱花钱。

但是,个人合法的收入,你是完全可以自由支配的,国家不会干涉你,限制你。但是,这些政治敏感的人,就跳出来指责李少莉:“现在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人发不了工资,你还在那里炫耀穿戴,不知低调,所以思想觉悟不高,作风趣味有问题,没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第五种,就是体制外的,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稳定收入的打工者。
这些人,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的经济压力非常大,有些人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对他们,我心里非常同情,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确实,我和李局长们,吃穿不愁,可以任意消费,但是,这是我们的错吗?她一个月工资上万,年薪十几万,用其中一年薪资的三分之一,买些自己喜欢的衣服配饰就是罪大恶极啦?就刺伤你们的眼睛?刺痛了你们的心脏?
打工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有是非观念的,有判断力的。如此痛骂李局长的,也只是你们当中的极少数人。

我真心地希望并祝福你们,今后一定会好起来的,并且会越来越好的。
以上几点,是我由李局长遭骂想到的。朋友,你以为如何?
2017年进入铁路,我们是转培的。转培就是学校没有这个专业,铁路来招聘后从新学校。2016年大专第三年校园招聘实习,那时候铁路还没来招聘,很是期待,又怕进不了,于是在来学校招聘的公司中选了聚光科技,当时个人感觉还可以,打算如果进不了铁路就留在聚光科技谋生。16年底铁路来学校招聘。我们几百人去面试,好像进了一百多个,当时开心极了,觉得端上了铁饭碗,对于我这种草根来说算是生活有了着落。进铁路就到了车辆段干动车,今年第5年了,一线搞检修,弹性工作制夜班一休一,24小时一休二。两种班制都干过,偶尔学习五休二,只能说累,工作压力大,懂的都懂。收入勉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工作强度大,要求严,标准高,越干越累。听说普铁的轻松,收入还和我们差不多,感到极度不平衡,不过想想20年后我们也该养老了,人家也会说我们,风水轮流转吧!

说说晋升吧,能晋升的一般都是有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嘴巴会说,干活得劲,脑壳转得快,还有一种就是特别会玩的,一天活不干多少,也不负责任,就是会玩,领导开心。其他的就乖乖干活吧,晋升无望。主要还是要有关系,关系强的,和我们一起入路的,两年不到就提了大工长,我们有的还在学习班待命!
说说学历,大专生当工长就是工人天花板,想提副科比登天还难。以前自考本科可以当本科用,现在不得行了,看都不看一眼,本科已经烂大街了。铁路本科生来了可以进技术,差点的当随车机械师跑车,呆应急台啥的。本科生进技术的容易提干,在其他岗位的容易提工长,有的领导要求工长必须是本科生,非常恶心。
还有干活,铁路工作要求严,标准高,任务重,压力一层层传导,干不好就拿下,漏检被领导发现随便小五百没有了,工长发现就是一张量化单,八十或者一百五警告一下!如果被局里面或者外局发现什么问题,在说确认漏检的话就是开分析会,随便小一千没得了,还有其他的事恶心人,比如背作业指导书,抄作业指导书啥的。

说说我自己的看法,一开始我也想当工长,想提干,往上面走,现在就想在一线呆着,除了干活被叫来叫去,偶尔考核哈,干活自己小心点,干慢点,仔细点。别出事,保付好自己。其他的就没啥了,下班就下班了,不用频繁的接领导电话,不用熬夜加班,不用零时开会,不用下班了还得留单位听领导BB。下班后时间就是自己的,挺好!
我觉得国家需要发展,产业需要升级。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我们干活只会越来越难干,标准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严,只有这样国家的产品才能走出去,在国际上才能形成竞争力,想想其他国家干活那么精细和标准,他们也是从粗制滥造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抱怨,社会需要进步,国家需要发展,人民想要过上好生活,我们只能这么做。#在国企上班的你迷茫吗#
上世纪80年代,部队军官很好找对象。阎连科提干后,战友给他介绍了个对象。不但家庭背景好,女孩的个人条件也不错。人长得漂亮,还是部队军官护士,谁知女孩看到阎连科的信后这样说。

1978年底刚开始征兵时,阎连科的哥哥很果断的对父母说“让连科去当兵吧,在家不行,没出路。”
母亲舍不得,说“都能掂刀砌墙了,眼看都快成匠人咧。”
阎连科很想当兵,也认为在家待着没出路,何况当兵不但能吃饱,混的好还能提干穿四个兜的军装。
于是在公社书记的周旋帮助下,阎连科穿上了军装来到部队。
新兵连的紧张训练对于当过民工的阎连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训练之余,阎连科还经常写写画画。
新兵连长看到阎连科写的一手漂亮的新魏体,就把他安排到了板报组。
还真别说,阎连科靠着在高中积累的知识,出的板报字体不仅漂亮,内容还丰富多彩。那时部队最缺的就是“笔杆子”,他因此成了新兵连的“拔尖人物”。
等到新兵下连时,“笔杆子”阎连科成了各个连队争抢的“香饽饽”。最后把他挑走的是营部教导员张英培,张英培曾担任过军区首长的秘书,特别热爱文学,也喜欢写诗歌。

来到营部没几天,阎连科就被张英培推荐参加了武汉军区在信阳举办的写作培训班。
参加这次培训的有30多人,但只有阎连科是刚下连的新兵。
在这次培训上,阎连科写了部短篇小说,虽然没发表,却得到了军区文化部领导的鼓励。
培训结束回到部队,阎连科没用多久就当上了副班长。教导员还告诉他“一年里发表3篇稿子就能拿到嘉奖,发表5篇就能记三等功一次。”
阎连科听后心想“写作不正是我的强项吗?为了提干那就试试吧!”
当时阎连科因为打靶已经立了个三等功,如果因为写作再荣立三等功,那就够提干的标准了。
可想在省级报刊上发表5篇文章谈何容易?
阎连科在营部报道员的岗位上开始发掘素材,从战士训练到名人名言,他不断的写稿投稿。直到当兵第二年底,他才算完成5篇任务,再次荣立三等功,并且顺利的入了党。

本来以为当兵第三年能顺利提干,谁知上级下发文件“未经军校培训的战士不能提干。”
阎连科当时已经超过了考军校的年龄限制,自知提干无望后,恰逢老家村支书来信说“你当过兵又是党员,还是高中生,不如退伍回来当村干部吧!”
于是阎连科办了退伍手续,拿着退伍证、170元退伍费和两个月的粮票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火车还没开动,一辆军用吉普突然冲进站台,车上的军人一连声的喊“阎连科在哪个车厢?”
阎连科下了车看到团长,团长告诉他“你为武汉军区编的独幕话剧拿到了全军文艺汇演的一等奖,军区政治部主任特批了20个提干名额,我给你争取了一个。”
就这样,阎连科实现了“提干穿四个兜军装”的梦想,从此吃上了公家饭。
这之后,阎连科笔耕不缀,渐渐的成为一名军旅大作家。
后来,他创作的《炸裂志》、《日光流年》等作品让读者和书评家给他冠上了中国“神实主义”的名头。

2003年,阎连科的《受活》发表,一举轰动文坛,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穿了26年军装,官至副师职的阎连科因《受活》脱下军装转了业,由此加入北京作协。
多年以后,阎连科的堂叔去世,他赶回家奔丧。
在灵棚里,一个堂妹对他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写一写咱们家的事呢?”
这句话对阎连科的触动很大,让他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和叔伯们。
回到北京,他一改昔日魔幻风格,以家乡田湖镇为蓝本,以自己的父辈为主角,写出了《我与父辈》。
当他去打印社拿书稿时,几个打字员对他说“阎老师,我们打印过那么多小说,唯独这本《我与父辈》看哭了。”
电子版发给阎连科儿子,儿子给他发了个短信“看完了,哭了。”
《我与父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首版会,交通大学的一个副校长和阎连科同岁,他找到阎连科说“咱俩同龄,但是看完《我与父辈》后也哭了。”

他还强烈要求阎连科一定要在交通大学举办一场读书会,只为让现在的大学生主动了解他们父辈的艰难,主动与父辈沟通。
后来在复旦附中的一场交流会上,一个16岁的初中女生说“以前我不知如何与父母沟通交流,在看完《我与父辈》后,知道了父母的艰难,也学会了理解他们。”
这个女生买了两本《我与父辈》让阎连科签字,一本送给父母,一本留给自己。只为时刻提醒自己要理解父母,要主动与父母沟通。
《我与父辈》是一本经历过的人读完后会产生共鸣的书,也是一本没经历过的人读完后能产生警醒的书。
父母读完《我与父辈》后,想把它送给儿女: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儿女读完《我与父辈》后,想把它送给父母:感恩,我们的父辈。
中国式父爱不善表达,却如山一样沉重,又如春雨润物一样无声。只有读懂我们的父辈,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我与父辈》值得一读。

闫连科母亲过寿,他回老家摆酒。当地的县委书记派人送来亲笔题的一副“寿”字,亲戚们见了,都以为他与县委书记交情很深。寿宴结束后,亲戚们把闫连科拉到一边说:有出息了可不能忘本。
闫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这是一个偏穷的村落。父母是农民,所以闫连科从童年时期就体会着乡村与土地带来的滋味。
上学之余,闫连科下田割草,喂猪放牛,每日除了疲惫就是饥饿。
闫连科的父亲有哮喘,一到冬天,闫连科和二姐就要出门承担起为全家人拉煤的工作。深夜出发、深夜才能回,来回要走160里。
那时闫连科的二姐就对他说“你是男娃,要努力离开家。”
从那以后,闫连科就产生了想急切脱离农村到大城市去的想法。
想去大城市只有两条路:一是考大学考出去;二是当兵提干。
77年高考时,闫连科落榜,那么只剩下当兵一条路。

16岁的时候体检政审都过了,得到了当兵的机会,临走前母亲却哭着说“娃太小了,不舍得。”于是,闫连科又去读了高中。
20岁那年,闫连科再次动起当兵的念头,母亲也知道这次是留不住了,便说“去撞一撞大运,撞一撞命运。”
来到部队后的闫连科开始表现并不太好,因为他的军事训练始终跟不上,以至于他自己都快没了提干的信心。
后来连长挑选板报组成员,闫连科因为字写得好再加上是高中生就被选上了。
等到新兵实弹射击考核时,闫连科用10发子弹打了100环,团首长不相信一个新兵能如此厉害,又给了他10发子弹,没想到闫连科打了99环。
团首长当场推荐闫连科参加师里组织的新兵射击比赛。
闫连科虽然不知道这个比赛究竟有多重要,但他知道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比赛当天,闫连科用10发子弹打了98环,拿了第三名,给团里争了光。

团里为了表彰闫连科,给闫连科立了三等功。这下子,他一跃成为同年兵中的佼佼者,离提干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等到新兵下连时,正好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闫连科作为“神枪手”,几乎铁定的要上前线。但教导员爱惜人才,把他送到了武汉军区举办的一个培训班学习去了。
学习结束后,闫连科直接来到营部当上了通信员。每日忙完工作,闫连科都会拿起手中的笔为下面的连队写新闻报道,涉及的东西很多,有大有小,比如某某连队训练又有新举措了等等。
直到当兵第二年时,闫连科写了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在报刊上发表,一夜之间成了全团的名人。当时的团长说“这么小就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以后还得了?”
后来,闫连科被调到机关专职写材料。因为基本功扎实,闫连科写材料手到擒来,所以业余时间很多。

但闫连科并未闲着,而是不停的写作投稿。因为那时部队有规定:在省级报刊上发表3篇文章可授嘉奖;发表5篇就能立功。
当时有许多人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命运,闫连科也想试试。
第三年时,闫连科终于靠着写作再次立了三等功,就等着提干之时,上级突然下来个文件说:未经军校培训不得提干。
闫连科已经超过考军校的年龄,眼看着提干无望准备退伍回家时,团长从军区政治部给他争取了一个提干名额。
就这样,闫连科实现了他走出农村的愿望。后来,他又靠着写作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最终在首都北京安了家。
闫连科成了名人,成了老家嵩县的骄傲。那年母亲过寿,闫连科赶回去摆酒。当地的县委书记派人送来了一副亲笔题的“寿”字,亲戚看了都觉得闫连科与县委书记关系匪浅。
等到寿宴结束后,亲戚们纷纷把闫连科拉到一旁说:有出息了可不能忘本,今年你侄女找工作,你得出把力。

还有亲戚说:你侄儿考大学,你得帮帮他。就连对面村庄的乡亲都跑来,托闫连科利用关系解决困难。
此时此刻,闫连科突然觉得自己虽然脱离了农村,走进了大城市,可始终与这片土地有着深刻的羁绊,他总觉得自己的作品少了点什么。
后来四叔突然去世,闫连科回老家奔丧,一个堂妹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东西,为啥不写一写咱们家自己的事呢?”
堂妹的这句话提醒了闫连科,回到北京后,他立刻动笔创作《我与父辈》。
在此之前,闫连科的作品一直都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但《我与父辈》却是以故土为底色,以父辈为主角,谱写了一曲父辈蚀骨情深之歌。
《我与父辈》成稿后,闫连科拿去给经常合作的打字社做成电子版,过几天去拿时,几个打印员哭着说:闫老师,我们打印过那么多小说,只有这一部是哭着打印的。

电子版发到闫连科儿子的邮箱,儿子给闫连科发了个信息“看完了,哭了。”
后来,《我与父辈》出版会定在复旦,交通大学的一个副校长找到闫连科要求在交通大学也举办一场,因为他读完《我与父辈》后产生深刻的共鸣……
在复旦附中的一场交流会上,一个16岁的女生说:我学习很好,但与父母关系很紧张,看了《我与父辈》后,才知道父母的艰辛,也开始主动与他们沟通……这个女孩买了两本,一本送给最好的同学,一本送给父母。
《我与父辈》就是这样一本经历过的能产生共鸣,感恩我们的父辈;没经历过的能有警醒之感,请读懂我们的父辈。
#作家阎连科# 1981年,没能提干的阎连科兜里揣着退伍证,手里拿着用110块钱退伍费给家人买的东西登上了返乡的火车。突然,一辆军用吉普直接冲进火车站台,车上的人一连声的喊:阎连科在哪?

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打小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顿饱饭。后来,随着年龄增大,他的愿望变成了“走出农村娶一个有城镇户口的媳妇”。
那时,农村孩子想改变命运,最好的途径就是当兵。于是,20岁的阎连科入伍参了军。
阎连科的运气是极好的,新兵连因为打靶打了100环被团部领导推荐参加师里组织的射击比赛。
在这场比赛中,阎连科拿了个第三名,为团里争了荣誉。比赛结束后,团里给他立了个三等功。
新兵下连后,正好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上级挑优秀的战士赶赴前线,阎连科因为枪打得好也在名单上。
当时的营部教导员喜爱文学,在看了阎连科入伍前写的一部小说后,把阎连科从名单上划掉,又调到了营部当通信员。
那时部队特别注重新闻宣传,就像注重计划生育一样,一个连队里如果没有一篇东西见报,工作再好也不能评上先进模范。

阎连科就轮流着给下面的各个连队写报道,不管写什么,一条小新闻稿、几行诗、思想火花都行。
在部队小有名气的阎连科被推荐到了河南信阳的一个创作学习班学习。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长篇、中篇、短篇,知道有杂志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培训结束后,阎连科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
阎连科因此在部队名噪一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后上级就把阎连科调到机关做新闻报道工作。
也是在这里,阎连科入了党,又立了个三等功,离他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可就当他做着提干穿四个兜的梦时,突然下发的一个文件将他打入谷底。
文件明确要求“提干的军官必须经过军校的培训”,而阎连科却没有这个机会。
阎连科自知提干无望后,恰逢家里的老村长写信让他回去接任村长,再加上他父亲病重,阎连科便答应了下来。

于是,阎连科办好了退伍证,拿着部队发的110块钱退伍费给家里买了东西,心有不甘的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正当他在心里与这个伤心地做彻底的告别时,突然一辆军用吉普车冲上了火车站台。眼尖的阎连科看到自己的团长趴在车窗上一连声的喊:阎连科在哪?
阎连科猜到了自己提干的事情有了转机。
原来,他为武汉军区编的独幕剧《二挂鞭》在北京举行的全军文化汇演上拿了第一名。当时文化处的干部对政治处的领导说:你看我们这些优秀的战士太可惜了,演出完就得退伍回家。
领导听了大笔一挥,批了20个提干的名额,其中一个就给了阎连科。
可当名额下来时,阎连科的退伍证已经办了,退伍费也花个差不多了。团长对阎连科说:既然都上车了,那就先回家看看,要是你还想提干那就7天后回部队,否则就算名额作废了。

回到家的阎连科因为父亲的身体犹豫了,当时在县邮电局工作的姐夫听说后立马赶回家里说:还是让连科回部队提干吧!人生的路接着往前走,不要回头。
就这样,阎连科在家待了7天后,返回部队换上了四个兜的军装,成为一名吃公家饭的干部,真正实现了他脱离土地的梦想。
但阎连科并未满足于现状,他还想着成名成家,所以他开始了疯狂的写作。那段时间,他在各类文学杂志期刊上不断发表作品,稿费也源源不断的寄来。
后来,阎连科在回忆自己这段时间的作品时,他说:小说的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灵魂。他觉得自己的心变得浮躁,只想输出,不想吸收新的知识。
直到1991年,阎连科因为写作得了腰突症,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开始读国外的经典著作。而这些经典著作正好与他病态的身体产生了无法言喻的共鸣。

也就是从这时起,阎连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作品,知道了自己以后的创作方向。然后陆续创作出了《日光流年》《年月日》等优秀的作品。
2009年,阎连科一反昔日“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以豫地风情为蓝本,以自己的家族男性为主角,创作出了《我与父辈》这本书。
《我与父辈》的初稿打印时,那些打字员哭着对阎连科说:阎老师,过去我们打了那么多小说稿,没有一本好看,只有这本,我们晚上把稿子带回家看,都看哭了。
后来,打字员打好的电子版发到阎连科儿子的电子邮箱里,儿子给他回复了6个字:看过了,掉泪了。
《我与父辈》刚出版时,发行仪式定在了复旦大学,和阎连科同岁的同济大学校长看这本书时看哭了,强烈要求把首发仪式放在同济大学。
后来,阎连科应复旦附中的要求与他们的学生做一次交流,一位16岁的女孩说:看完这本书,我知道如何来处理我和父母的关系。她买了两本书请阎连科签名,一本给自己,另一本打算送给父母……
所以,很多读者在读完《我与父辈》后,都会有一种经历过的人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警醒与启迪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