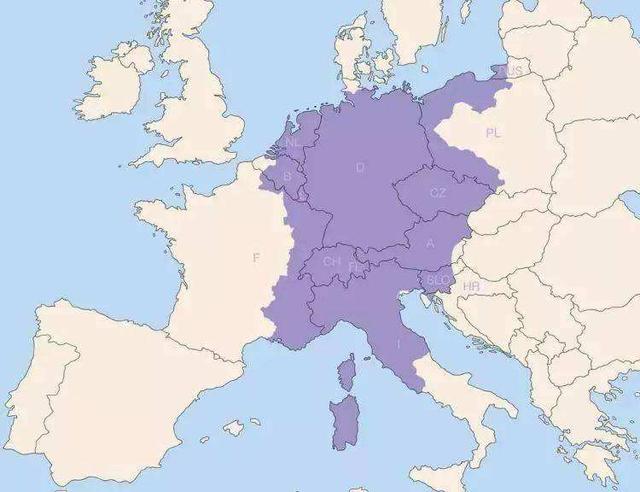喜欢浆水还是酸奶?
我跟人开玩笑说,若遭荒年,天水人能扛得久一些,因为天水人有浆水,极能拉长事物供给的战线;而兰州人比天水人扛得更久,因为兰州人的浆水面里没有菜。
在外漂泊的西北人,为什么会偶尔思念那寡淡廉价且甚无营养的浆水呢?直到去年我才知道,常常惦记少时的乡味,是肠道菌群的原因。因为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的培养,我们的肠道菌群早就在家乡定型了。所以吃别的地方的食物总有不彻底不踏实的感觉,日久更是迫切地思念家乡的某一些食物,哪怕只是些单调粗糙的小吃……
我少时有“两条建议”和“一记巴掌”一直印象刻骨……
我读初中的时候,三舅已经去太原理工上大学了。通信是那个岁月的时代记忆,我说的建议就是三舅在信中提出的。第一条,对我们全家的一条建议,是少吃腌制类的事物。我小时候我们家确实很能吃腌咸菜,有两个陶制的缸,约莫80公分高,一个专盛浆水,一个专装咸菜。腌制食品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天天都吃。其实也不是我们家,物资匮乏年代过来的人,哪个不会腌咸菜,哪个人肚子里没有装过几十斤咸菜呢。我记得我所在的那个家属院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这样的缸,至少也得是个大罐子。

第二条,是三舅专对我的一条建议,让我多去看看电影,增长见识。所以我最早的电影启蒙导师应当是三舅,我喜欢进电影院的基因应该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只不过前进路上,起步多有坎坷,我与电影缘分的最初阶段都是在录像厅里度过的,我以我的青春记录了“电影”从录像带到光盘再到电影院的嬗变。而我看过的大量的所谓电影,也不是三舅期望的那样。也许苗子本身更为重要,所以即使以粪水浇灌,也能长成。时至今日,我仍然是一名坚定的电影爱好者。我的书架上一直摆着青春期的电影偶像周星驰的带框照片;我书柜里仍存有一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按照英文字母顺序记录着我看过的所有电影,真的是所有——记录截止2014年。
我知道大家对电影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但还是说回浆水吧,毕竟还有“一记巴掌”没有交代。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午饭正在进行中,父亲忽然一巴掌扇在我后脑勺,我差点把手里的碗摔了,我没有嗫嚅的问怎么回事,因为我完全沉浸在惊愕中,还没有在大脑中加工出来前因后果。父亲开口训斥了,其实是对那一巴掌的解释:“咋能把菜夹到浆水面里呢?”我记得,我没有说话,只是有眼泪在眼眶里游走,以前挨打的事出有因我是能理解的,只是这一巴掌颇多委屈。我从小挨过父亲很多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比如用皮带抽打我的头和脸,但直到中学时知道我一位同学是被家里人吊起来打的,我才惊觉自己的严父手下留了许多情,我竟是幸运儿。很多事情在做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象父亲的皮鞋踹在我屁股上的感觉了,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不能因为后果就不去做。比如,我把成衣店里的光身子模特化妆一番,用红纸裁剪下长长的舌头粘在假人嘴上,脖子里还系上麻绳,放在了女厕所的墙角里。我小学时候那个家属院只有一个公厕,不仅我们整个院子、院子里的两三个单位,还有门口1路公交车的司乘人员,都在用这一个公厕。于是,就看到有吓得大喊大叫的女阿姨提着裤子冲出来……我们在旁边笑得人仰马翻,这样的快乐,用一顿打来换,简直划算,儿时的人生就要这么快哉。在我小时候的生活逻辑里,父亲打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将来也得这么教训我儿子,所谓天理循环嘛。能三两下就用武力解决的,干嘛要婆婆妈妈用语言沟通半天,西北人至今还是这样活着。

总之,在我的家乡,浆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用我初中班主任教训我们的话说:“你们天水人说话都带着浆水味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本地人,本地师范培养出来的。不过,人家的普通话确实说得好。在我们那里,能分得清前后鼻音的,都是很洋气。我记得去年上课时,一位学员和我聊天说:“老师,我听出来您不是本地人,您都可以说出来后鼻音,我们这边人说话都靠前。”我心里暗忖:天哪,我们不光是秦人的先祖,更是后鼻音的祖宗!因为我们能把一切字都说成后鼻音。
可话说回来,浆水这样东西毕竟是我们西北人的敝帚自珍了,招待远客贵客,万不能将之,除非对方点名要吃。直到去年春,兰州大学的一项科研成果总算是给浆水争得了些尊严,该校环境微生物课题组花了4年时间,在浆水中分离出一种新菌株,竟能通过降解动物体内的尿酸,控制尿酸积累,缓解痛风。通过食疗缓解痛风,在世界应属首例。顿时,这条新闻登上了热搜,我老家的人们纷纷转发,就觉得第一次被浆水给自己脸上贴了金。
只是过了不许久,该研究成果的后续,浆水酸奶就问世了,一盒12瓶,卖325元。可怜的浆水酸奶,一问世就是一步死棋。还是收归体制,改为特供品吧。再或者,申请注册为药品保健品,专卖给天下痛风的人,也许能兴旺起来。
封城以来,我只买了三次菜,母亲从老家带来的浆水,让我们的食谱撙节而可持续,还教我想起好些小时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