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丈夫单位破产了,我丈夫找临时工作没有人用他。
我和丈夫天亮就出去了找工作了,我在本地看到电杆上贴的招聘启示。上面只写了电话,招女工几名,没有写干什么的,地址也没有写详细。
我就打了招聘的电话,招聘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活,我说:我会包饺子,做饭什么也会干。
招聘的人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来吧!我说你那是干什么的,招聘人说:是开饭店的,
我和招聘约定了一个地点是邢台市附近,她让我们过去等她。
到了约定了地点就给招聘人打了电话,人家说等她一会儿,过来接我们。
等了一会,招聘坐着出租车过来接了我们,招聘人拉到她的胡同里一个平房,她把我们带到平房屋子里。
我看到里面屋里有监控器器和一张床,我问了招聘人说:你的饭店在哪里?
拓聘人说:没有饭店,前面胡同大路上有个足疗馆门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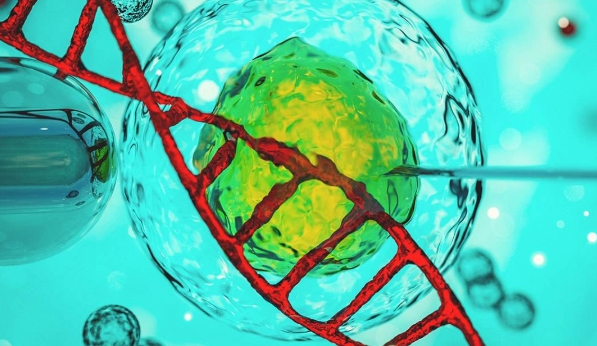
我说:你不是在电话里对我说:有个饭店吗?
招聘人说:没有饭店,说谎了,不这么说你能来吗?我听了很生气,心里想,这是进了足疗馆家了。
招聘人对我丈夫说:她也是本地人,她自己开的足疗馆。她说她有好几个姑娘在地住处打工。
还没有聊完,就来了一位客人,招聘人说:洗脚吗?有特殊服务。
客人说不了,就走了。招聘人对我丈夫说:她这个足疗服务是给客人按摩冼脚,
与聊天的,接待客人。客人想怎么着,就必须服从。我生气的说:不行的,我不干。听了就听不进去了。招聘人对我说:你干不了这个工作,人家别的姑娘一天挣好几千,一个月下来挣好几万。我听了,心里想:挣钱快,又多,肯定不是好事。
我丈夫对我说:走吧!
我就和丈夫出来了,走到半路上有个饺子馆招工,进去问了老板娘招聘吗?
人家饺子馆说:只招聘男工,不招女工。

工作不好找,我和家人就做车回家了。
说个真实的事,那是在1974年左右,我跟着生产队赶头车的大老板子,往城里送粮,因为他小舅子是大队书记,儿子被招工到城里的一个工厂上班,娶妻生子,有了一个7岁多的孙子和一个5岁多的孙女,那时往城里送粮,都是半夜一点左右就走,到城里40多公里的路程,天刚亮,到粮库排号卸完粮后,冬天天短,天就快黑了他嘱咐我喂马,他就把给儿子带去的豆包和饺子送到儿子家去,当时住的都是大车店,就是一间大长筒房子,一铺东西大炕,外边有马槽,我添上草料,送粮的都是县城周边屯子的,就一边和临近的人说话,一边吃着自己带的干粮和咸菜,大车店里有开水,赶车的大老板到儿了家已经有点黑天了,那时,整个县城也没有几栋楼,居民住的都是平房,他到儿子家推开儿子家的院门,看到孙子和孙女正在院子中间玩儿,儿子媳妇儿在忙着做饭,因为冬天穿着大皮袄,戴着大皮帽子,一天沒洗脸再埋汰点,身上背个破口袋,孩子也沒看清,吓了一跳,也不敢动,就朝屋里喊爸妈快出来呀,来了个要饭的老庄稼人!这时他儿子儿媳跑出来一看是他父亲,就吆喝孩子说,说什呢?还他妈的骂是要饭的老庄稼人?细看看,你骂的这老庄稼人不是你们的爷爷吗?

母亲从县城来城里养病,从平房住到了高层。一个月后母亲渐渐好转,逐渐可以自己下楼走动。然而母亲一个举动,让我简直哭笑不得!
我自小没了父亲,母亲拉扯着我和弟弟,我家在一个三四线的小县城,家里有一个小院,两间平房加一个自己盖的厨房,母亲是一个厂子里的女工,白天上班,晚上回来。我和弟弟就在厂里的子弟学校上学。
那时候人也朴实,没人偷孩子,下了学,同学们都在一起疯玩,等家长们都下班了,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我比弟弟大着四岁,弟弟从小就是我的跟屁虫,我这个姐姐义不容辞的保护着他,弟弟调皮,不爱学习,交不上作业时,都是我这个姐姐帮他写。
那时候能考上中专都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毕业国家给分配工作。我想早早挣钱帮妈妈,就在初中毕业就考取了中专,到市里去上学。

妈妈含着眼泪送我到学校,每个月省吃俭用给我寄生活费。日月如梭,几年的学业没有白费,毕业后我进入国企并参加招干考试,顺利成为机关里的人员,由于我很上进,很快得到升迁。
我认识了同单位的老公,志同道合,单位给分的福利房,我们结婚生子,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弟弟不是个上学的材料,妈妈为他愁白了头,初中毕业就待业在家,那些年工厂招工会先招子弟,妈妈托人情送礼,终于把弟弟送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母亲熬到退休,又不肯歇下,自己摆摊做些小生意,攒了些钱,也给弟弟娶了媳妇。
弟弟两口跟着母亲住在老院子里,自家小院翻修了,又盖两间房子,几年后有了孩子,母亲照看着孙子,院子里养了一群鸡,弄一圈栅栏围着,每天出去菜市场转转,捡菜叶子回来喂鸡,下了鸡蛋,会攒起来一些,等我回来拿。

我想接她到城里,她死活不肯,舍不下老院子,老邻居。
我们买了一百多平的商品房,在二十层。母亲就在我们搬家的时候来过一次,住了不到一周,死活要走,母亲说这是住的鸽子楼,火柴盒,不自由,不接地气,不能开着大门,总之就是不住了。
母亲回了县城的院子,依旧喂起了小鸡,小狗,还开了几洼地,种的豆角青菜小白菜。厨房里盘着吸风灶,早年的风箱升级成了鼓风机。
孙子大了出去上学,母亲空闲下来,会到附近的小路溜达,年轻时养成的拾柴禾烧火的习惯到现在还是依旧。虽然早已烧上了煤炭,可还是有事没事的捡一些树枝堆到院子,没事掰成小枝,码放整齐。
母亲无声无息的老去,终于有一天一个小感冒引发大病躺倒了。县城里检查了一番,感染了肺炎,不放心又接到市里,情况还好,住院两周后回我这里住进了她嘴里的鸽子窝。

母亲渐渐好转,我会扶着她下楼走走,晒晒太阳。逐渐的,她可以走动,不要我管。她会用老人机,我知道她走不远,就在小区里转悠。
一日,母亲兴高采烈的回来了,手里拿着个塑料袋子,里面横七竖八的放着干树枝,原来楼下修建花木,剪下很多的枝枝丫丫。
母亲捡树枝的爱好被重新唤醒,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各种袋子,上下几次从楼下捡树枝回来,这一下午是头也不疼了,脚步也不慢了,有点驼背的腰都好像直起来不少。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她一趟一趟的下楼上楼,下楼上楼,阳台上不大一会就被堆满。我开始阻拦她,责备她,逐渐开始生气,大声,吵她!
不行,阻挡不住,她依旧跑上跑下的捡着,我忍不住吼她,问她到底想咋,我们住高层,不烧炉子,用不着柴禾,堆到阳台,不但乱七八糟,还有安全隐患!
我要给她扔下去,母亲不肯,搬个小凳子,拿着我心爱的剪刀剪着树枝,嘴里骂我不过日子,威胁我敢把她的柴禾扔了就和我没完!

我哭笑不得,老公和儿子回来看着前后两个阳台上捆扎的整整齐齐的小树枝,满脑袋纳闷着,我使使眼色撇撇嘴,他俩也不敢吭声。
我给弟弟播了电话,弟弟第二天就开车过来了。
弟弟早几年在县城里也买了房子,一家三口早都搬了进去,老妈坚持不住楼房,独自一人坚守阵地,弟弟无奈,只有两头跑着,一边是老妈,一边是媳妇。好在弟媳妇并不多事,也是时常回去照顾老妈。
弟弟开车要接母亲回去,母亲向弟弟控诉着我的不好,我挽留着,母亲骂着,非要让弟弟把她那堆小树枝小柴禾都搁到后备箱里带走,并且要看着装到车里才行!
弟弟气恼着跟她翻脸,说她想害死儿女,搬到高层会失火!弟弟往下搬着,直接扔到垃圾桶,母亲骂着也不听。我不吭声,这可是你最爱的儿子扔的,我看笑话!
扔完了,弟弟给姐夫塞了两条好烟,老公笑的肚子疼,连忙推搡着不要。

弟弟硬拉着老妈走了。我望着远去的汽车,心里思谋着,母亲老了,糊涂了,不知不觉,眼泪淌了下来。
缅怀父亲
第一篇 学生时代
我的父亲是1943年11月18日出生的,家中兄弟姊妹三个人,爸爸排行老二。爷爷年轻的时候从河北高碑店来到大兴,所以父亲出生在大兴黄村。爷爷没有文化,不识字,为了生计,爷爷初到大兴时,做了人力车夫,后来因为日本人控制的丰台铁路招工,爷爷抱着试试的态度应聘,后来成了铁路的一名电工,经常爬电线杆子,虽然工作辛苦,索性有了稳定的收入,后来日本人在丰台区看丹桥南红房子那边盖了很多平房,当时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解放后,政府和北京铁路局将这些房子给了铁路职工,这样爷爷有了自己真正的家。
爷爷自己没有文化,经常和奶奶说,我虽然没有读书,将来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上学。因此,爷爷一直很重视子女的学习,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也要挤出钱来让孩子上学。我的大伯是1935年出生的,学习很是争气,学习一直很好,爷爷听说通州潞河中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可以用粮食当学费,后来就把大伯送到了潞河中学读书,听爸爸说,当时交通不发达,大伯需要从丰台坐火车到通州,爷爷每次开学前都会送大伯到通州,然后直到放假才能回家。大伯后来考进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国家免学费还给生活费,大大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爷爷非常高兴,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不幸的是,大伯大四那年,爷爷因喉管癌去世,当时爸爸才14岁,姑姑9岁。听奶奶说,爷爷的出丧费是爸爸挨个到领居家磕头借来的,我为有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

爷爷走了以后,家里的负担就落到了大伯身上,大四那年,大伯从生活费中寄出点钱寄给奶奶,奶奶经人介绍做了点零工,勉强维持家里的生计,大伯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大伯每个月都能寄来生活费,虽然不多,也能不挨饿了,但家里依然是街道最穷的家庭。听奶奶说,有一次领居家丢了东西,直接就怀疑是奶奶,虽然只是一个误会,但奶奶很生气。
爷爷走的时候,爸爸14岁,正是上中学的时候,爸爸一直以自己的兄长为榜样,在丰台12中读书的时候,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但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奶奶希望爸爸能早早上班。爸爸有自己的想法,大伯结婚后,还是会经常回北京看望奶奶和弟弟妹妹。爸爸把自己想上大学的想法和大伯说了,大娘当时就说,只有你能考上,哥哥嫂子就供你读。多年以后,爸爸回忆那次高考,说:“如果第一次考不上,就要去工厂上班。”但爸爸真的很争气一次就考上了,当时报的是北大,差3分没考上,1961年,爸爸来到了北京林业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学习林业专业,开始了爸爸的大学生活。奶奶非常自豪,奶奶曾经说,“家里一共三个孩子,当时邻里街坊就咱们家出了两个大学生,再也没有人因为咱们家穷低看我们了。”大学期间为了节省生活费,不舍得吃,终在大三那年得了肝炎,后来休学一年,大伯把爸爸接到家里,调理了一年,回到学校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在那个造反就是有理的时代,正常的学习变得非常奢侈!大学毕业后,响应党中央的支援西部边疆建设的号召,爸爸放弃了去北京林学研究院的工作,毅然决定来到了内蒙古包头林业总场,开始了支援西部的工作生涯!

2003年,于波拍完《水月洞天》,片酬到手还没热乎,他就拿出260万全部积蓄,在北京入手了两套四合院。
听说于波买四合院的消息,亲朋好友嗤之以鼻:有钱买这种破烂,早晚掉坑里。
没想到如今,已经过气的于波坦言:现在我不用拍戏,这两套四合院就够我下半辈子用了。
1976年,于波出生在辽宁的沈阳。小时候,于波的家住在一排平房里。
于波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不让父母操心,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11岁的时候,他就养了100只鸽子。
每天放学就急忙回家照顾鸽子,他可以坐着三个小时不动盯着鸽子的一举一动。
每天精心照顾鸽子的经历,让于波小小年纪就有着一般孩子没有的责任感和稳重。
20岁那年,北京的一个单位来沈阳招人了。
于波一打听人们才知道,原来是钓鱼台国宾馆来招聘工作人员。

要求必须是年轻人,外貌和综合素质都要一流。
彼时的于波,已经愈发帅气,高大的身姿和英俊的外表,谁见了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
农村人的他,如果走进国宾馆里工作,大有一步登天之感。
工作了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身边同事报考电影学院,便定下了生活的新目标。
经人介绍,于波认识了李双江等老艺术家跟从他们学习声乐,他们建议他去考表演。
后于波就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作,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他的同班同学有姚晨、凌潇肃、叶静、杜淳、潘星谊等人。
虽然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于波也毫不担忧恐惧,他总是很认真地钻研表演。
2001年,《萧十一郎》剧组正在挑选演员,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于波就跑去试戏。
穿上戏服后,剧组一致认为于波的形象十分贴合连城璧的角色。

就这样,一个还没毕业的表演系学生,第一部剧就饰演了男二号的角色。
2004年,于波作为主演拍摄了让他火遍大江南北的《水月洞天》。
当年这部玄幻爱情剧一播出就反响空前,创造了当年的收视冠军。
虽然剧中人物形象在今天看来十分非主流,但沉迷剧情的观众早已忽略这些细节。
顶着一头“泡面”发型的于波和参差不齐刘海的蔡少芬,成了多少人心中的“意难平”。
他们用演技盖过了浮夸的造型,成就了经典。
于波在拍摄《水月洞天》之后,名气大增,接著又接了好几部戏。
有了钱之后,于波在北京购置过两座四合院,分别位于雍和宫、什刹海。
那时候北京的房价还不算高,他又喜欢传统的建筑,认为这样的四合院很有历史意义。
所以趁着现在有了足够的资金,买了两栋。
有朋友说他没眼光:“你买这两套破院子,什么设施都没有,还那么破,有那钱不如买商品房实用。”

但是于波却有自己的看法和坚持,他说自己从小住在农村平房,听着屋檐下着雨的声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机勃勃的,他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
所以哪怕亲朋好友都一致反对,于波还是坚持买下了这两处四合院。
为此于波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省吃俭用。
本以为演艺道路会就此一帆风顺,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
因为经纪公司破产,于波也没有后续的资源,这对于一个正值事业上升的演员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波的人气越来越低,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事业。
其实并不是于波退圈了,而是他手里的资源变少了,他本人其实一直坚守在演艺道路上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今是个“流量至上”的时代,很多空有颜值的“流量小生”把好资源都给抢走了。

像于波这样的老演员虽然演技非常好,但他们也只能慢慢被“淘汰”。
虽然演艺事业不顺利,但那两套四合院,给于波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如今北京房价疯涨,于波那两处曾被亲朋好友视为破房子的四合院,已经涨成了天价。
无心插柳柳成荫,于波本只是想拥有自己梦想中的家,没想到却因此做成了一笔大投资。
于波身价暴涨到了10亿,他直接成为了人生赢家,当初那个等着他出丑的朋友见状,后悔万分。
投资真的需要眼光和良机的,于波抓住了机会,一个翻身成为了富豪。
现在的于波有戏的时候,便会去拍戏,空闲的时间,便会在四合院里喝喝茶。
看着自己喜欢的动物,偶尔也会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非常惬意。
相比于其它的演员,于波的起点并不高,没有背景与人脉,靠自己如今也活也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虽然没有大火,但这样的生活或许正是他所想要的。#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