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督导检查郑州市邮政快递业疫情防控工作!
5月11日上午,随着郑州市主城区部分地区解除静态管理,河南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强第一时间带队前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省邮政机要通信局、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郑州市顺河路营业部,现场督导检查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和行业运行保障情况。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王志强重点了解企业的防疫物资准备、人员上岗、客户服务情况,对邮政企业作为国家队在疫情防控期间扛起保通保畅的行业责任给予充分肯定。在省邮政机要通信局,重点了解近期机要车辆通行、业务调整和保障情况,强调指出机要通信是党的红色传令兵,是党和国家赋予邮政企业的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越是困难越向前,一定要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保持畅通。在一线营业网点,王志强重点检查企业防疫物资储备、人员进出扫码登记、现场测温及生产场地消杀等情况。

王志强强调,当前我省尤其是省会郑州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防疫信息,实时掌握城区内封控、防控和防范区域变化,加强做好自身防护,维护寄递渠道安全平稳畅通。叮嘱邮政快递从业人员要把思想和认识同党中央、国家局和省局的各项决策部署统一起来,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工作。
省快递协会、省局普遍服务处相关同志陪同督导。
拟稿人:张智华
编辑:王聪方
县委办四个『股级』科室是哪些?,四个『正科』局室是哪些?
股级
1、秘书科
2、政研科
3、综合科
4、信息科
正科级
1、机要局
2、保密局
3、信访局
4、督查室
#职场# #吐槽# #公务员# #铁饭碗# #体制内#
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吉林省密码管理局(省委机要局)原局长许振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清廉十师#【师市党委机要保密局扎实开展第二十四个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7月以来,师市党委机要保密局开展了以“讲政治、守纪律、敢担当,推动兵团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在第十师北屯市落地见效”为主题的第二十四个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进一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师市党委机要保密局通过专题学习、观看警示教育片、向先进典型学习、党纪法规和德廉知识测试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党纪党风观念和廉洁自律、廉政勤政意识,使党员干部筑牢反腐倡廉思想防线。(师市党委机要保密局供稿)网页链接
来 源:第十师北屯市融媒体中心
编 辑:潘新萍
责 编:张容铭
监 制:刘春燕
签 发:李洪君
近日,吉林省密码管理局原局长许振昌被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单位是保密单位,也叫吉林省委机要局。

据了解,许振昌已经退休,生于1959年,长春人,属于本地干部,他24岁工作,31岁入党。长期在吉林省委工作。
在吉林省委工作期间,他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督查室、省委机要局等多部门工作过,经验丰富。60岁的时候,他按照有关规定退休。
没想到已经63岁的他被查,辜负了组织多年的信任。
#长春头条#
#高考# #大学# 非985和211,电科院分数接近211或985,而且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不影响报考其它大学。大四统一组织国考,就业大多数是政府机要岗位,地方到中央都有,最次也是县城机要局,还有市级,好的就是中央部委、外交部等。
12月22日,市委保密机要局二级调研员曹道君一行来延川县检查指导保密机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县委保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县委副书记张晶主持会议。

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之后,原来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保密局”已失去作用,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其统统撤销,新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所有的情报工作。
稍后,这个委员会又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大权由蒋经国操纵,原来由保密局“管束”的张学良自然也移到了蒋经国手下。
蒋经国接手后,对“管束”工作进行了调整:日常的看守交由“警备司令部”负责;张学良的动态由他亲自过问;为便于“管束”,速将张学良迁出偏远的井上温泉。
从井上温泉迁出之后,张学良和赵一荻在高雄、基隆短暂住了一个时期,接着又再次迁移到台北郊外的阳明山,蒋经国选了靠近阳明山庄的一幢别墅给张学良。其时,阳明山脚下的士林镇,已被蒋介石和宋美龄确定为日后定居的官邸。
转眼到了1959年3月,一天,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满面喜色,兴冲冲地登上阳明山,直驱张学良的居所。

张群是国民党的元老,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除宋子文外,张群可以说是与张学良交往最多、最深,并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有密切关联的人物。
1954年6月,张群担任了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在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开通了一个彼此都可信任的渠道。
1955年春,蒋介石首次召见张学良,即是由张群出面作的具体安排。张学良向蒋介石呈送《自述》和信件,也是通过张群之手。
1957年9月,蒋介石70寿辰,张学良托张群向蒋赠送礼物,以示贺寿。蒋介石也回赠了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让张群带给张学良,意为让他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
“汉卿,你自由了!”张群一见到张学良就兴奋地说道:“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解除军委会对你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22年自由突然降临,屋子里寂然无声,好久,才传出赵四小姐低声的啜泣。张学良从椅上慢慢站起,一只手抓住胸前的衣襟,一只手扶住桌子,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当夜俩人一宿未眠,默坐到了天明。
几天之后,张群邀约了张学良的老朋友莫德惠、王新衡、冯庸、何世礼等人来到阳明山,向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表示祝贺。张学良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可口饭菜,然后与大家频频举杯畅饮。
1961年初,张学良向前来看望他的蒋经国提出,说住阳明山上,他年纪大了,上下都不方便,距台北市区又远,朋友来访和他去看朋友都诸多不便,能否由他自己出资,在靠近城郊的地方盖一房子,搬下山去。
蒋经国当即表示同意,而且自告奋勇说地基由他去选,一定让张学良能够满意。大约过了一个月,蒋经国派车将张学良接到台北市西郊的北投复兴岗,让他察看定的地基。
张学良登上小山岗,见这里绿树成荫,视野开阔,站在山岗上能将台北市区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附近建筑又少,环境安静,空地上还可建个花园和网球场。

张学良十分满意,问赵四小姐,她也觉得此处环境幽雅,槐绕柳合,是家居的绝妙之处。两人都表示,同意蒋经国的安排,修房工程可立即动手,以便早日搬来。
建房之事既然由蒋经国张罗,速度自然很快。到8月底,一幢两层的灰色小楼已经落成。前面是一个大院,两边是满栽花草的花园。院内院外都移栽了高高的柳树,风吹枝摇,荡出爽爽的凉意。
与这个院子一路之隔,还修有一个灰墙环绕的安全人员驻地,正对的大门口,钉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警备处”三个大字。
搬家那天,张学良显得格外兴奋。来台以后,无论是在新竹井上温泉,还是阳明山的寓所,都是当局为“管束”他而选定的地址,每道门,每扇窗,都带着羁押的浓重阴影。
现在,他终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拥有一幢自己的住宅,能够吐纳自己的气息了!当年手握重兵的少帅,现在为了这一块小小的领地,激动得绕前绕后,老泪纵横。

得知张学良乔迁新居,张群、王新衡、莫德惠等一批老朋友都赶来恭贺。蒋经国没有露面,但却差人送来了一套崭新的红木客厅家具,以示祝贺。
张学良的“管束”虽然已被解除,但并未获得普通人那样全面的自由。
搬来北投时,张学良抛下了一大批敷染着幽禁阴影的物品,过去保密局配给他的汽车也坚持退掉,另外托人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牌轿车,闲着无事,便开车进城转转。
但他去的地方有限得很,不外是拜访一下莫德惠、张群、王新衡等老朋友,有时也去台北看看父亲的五姨太王夫人、六姨太马夫人以及她们的子女张学森、张学英、张怀敏等人。
若他要见蒋介石,须通过张群的联络;若见蒋经国,须通过王新衡预约;见宋美龄则通过黄仁霖。但外人想要见他,却不那么容易了,如非通过以上几位张学良的老朋友搭桥牵线,人们很难见到这位传奇性的人物。

按台湾当局的不成文规定,所有要见张学良的人,都应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的逐级申报,再由张学良宅对面的“警务处”予以放行。因而对外界而言,张学良仍然生活在严密的帷幕之中。
1933年6月,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机要处执行科长卓雄带领被称为“秘密武装队伍”的保卫队在长汀一带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命令赶回了河田,机要处长向他们传达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赋予的特殊任务。
“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他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大部队来接你们。”
@说说历史那点事
卓雄受命后,反复掂量着这次任务的分量,思谋着执行任务的良策。
由于国民党军陈济棠的部队对苏区的军事封锁,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道、小路、城镇和村庄,到处都布满了国民党军队。

这就给这个不到20岁的卓雄和他的“秘密武装队伍”带来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不久前,卓雄在迎接并护送博古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时,就曾遇到极端危险的情况,并创造了死里逃生的奇迹。
面对新的重大任务,卓雄来不及多想究竟是要“搞回来”一个何等“重要的东西”,他要全力关注的是如何确保万无一失地完成党的任务。
经过紧张、迅速而又周密的准备,一支由12人组成的“秘密武装队伍”踏上了征程。
卓雄和他的战友们每人带着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
因苏区被敌人长期封锁,食盐奇缺,他们每人还带了一小袋食盐,以便沿途食用。
他们专寻山间偏僻小径,夜间急速行进,白天隐蔽休息。
途经上杭县和永定县,按照预定时限到达了大埔县的秘密交通站。

大埔交通站是由好几个接头站构成的。
这些接头站大多是以店铺作掩护,各个接头站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相互之间”各自营生”,谁也不知道谁。
即便是“秘密武装队伍”的队员也不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一家暴露殃及其他人,而且可以预备一个站发生问题,还有另外的站来替补。
当然作为执行科长的卓雄,对于这份珍贵的“家产”还是一清二楚的。
交通站的基本职能是负责给住在野外的“秘密武装队伍”送饭、送消息。
离开时由交通站派出向导,负责送到下一个交通站。
卓雄到达大埔交通站时,终于见到了那个“重要的东西”。
原来是两个陌生人,一个是长一脸络腮胡子、穿着一身像是紫红颜色的风雨衣服装的外国“神甫”,另一个则是护送“神甫”来的中国胖子。
他俩都是从潮汕乘船来到大埔的。

交通站的同志告诉卓雄,这位中国胖子叫潘汉年(并非建国以后曾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
潘汉年把这位外国“神甫”交给卓雄就回香港去了。
卓雄的“秘密武装队伍”护送着这个神秘而又重要的外国“神甫”,在交通站的向导带领下,连夜踏上了返回苏区的归途。
上海市国家保密局的具体职责是什么?这个部门,我不是很了解啊。
三天的上海高考,需要那么多的上海行政部门一道出场为之贡献力量!就连那个我虽略知一二但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保密局也出马了!今日市教委主任王平同志的一番话令我吃惊不已,也长了不少见识!
我本以为上海高考,出动上海5个行政部门——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交通委——也就足以应付了。而王平同志今日在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我们将依托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招生考试联席会议机制,强化教育、考试、卫健、公安、保密、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交通、水务、气象、电力等部门紧密协同,织密保障网,为高考和中考‘保驾护航’。”指名道姓的就11个行政部门,一个“等”字说明为确保上海高考、中考顺利完成,还需几个行政部门做一些辅助工作。哪11个?

“教育”“考试”分别是指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这个好理解。“卫健”“公安”,指的是市卫健委、市公安局。“生态环境”“应急管理”,那就是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老早是没的,好像是前几年成立的。“交通”“水务”“气象”“电力”,也很简单,指的就是市交通委、市水务局、市气象局、市电力局。
就是那个“保密”二字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想了半天,脑中翻遍了上海所有行政部门,就是想不起来。忽然想到上海高考、中考涉及重大保密工作,这“保密”是不是指国家安全机关。我顺着这个思路想起来了,老早经过天钥路、中山南二路路口徐汇区公安局时,记得有三块牌子——一块是“徐汇区公安局”,挂在大门左边;另两块分别是“徐汇区国家安全局”“徐汇区国家保密局”,在大门右边。对了,“保密”指的应该就是上海市国家保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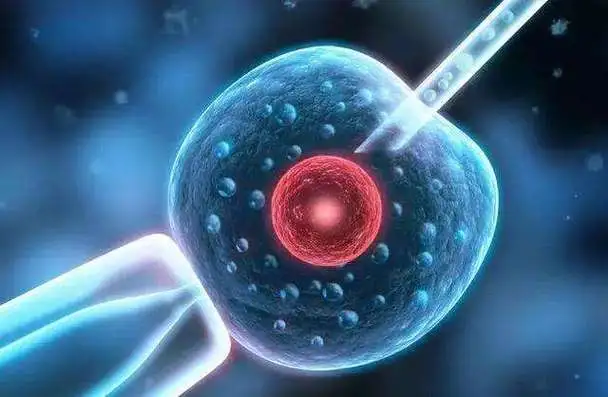
有一句说一句,与之一道合署办公的国家安全局,我也有所了解,其职责主要是负责境内反谍,维护国家安全的。但对国家保密局,只是晓得有这个单位,却不知其具体职责,只能大概推断其是负责行政系统内部机要文件的保护存放工作。我记得,高考试卷应属于特级机密文件,历史上那些盗窃高考试卷的作奸犯科之徒都是被以窃取国家机密罪论处。
向上海市国家保密局的同志们致敬!为了高考、中考的公平公正,为了防止奸邪鼠辈对高考、中考试卷的窃取,他们在疫情期间仍然在岗敬业,绝不平凡,殊为不易!#上海头条#
#老照片#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机要员方卓芬与孩子留影。方卓芬,广东惠来人,汕头市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前身)。
在校期间,方卓芬与进步同学一起参加学生救国会,在校内外进行救亡活动,结识了广东老乡徐扬。徐扬曾经是中共党员,因被捕与组织失去了关系,但他仍积极参加救亡工作,经常组织进步青年到他居住的寓所,共同学习和讨论。徐扬组织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共有九人,同为小组成员的方卓芬和许涤新在这里结识。

许涤新,广东揭阳人,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和上海劳动大学。 193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先后担任“社联”常委、党团书记,常在《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刊物发表有关经济和国际问题的文章。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关进苏州陆军监狱。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交涉释放,组织派他到上海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工作。
在上海期间,许涤新经常在徐杨组织的学习小组中发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当时许涤新刚出狱不久,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提出的看法与观点确是铿锵有力。方卓芬比许涤新小十岁,对这位老乡十分敬佩,并与他进行热烈的讨论。
由于上海的局势越来越严重,学习小组的成员先后离开上海。方卓芬去江西南昌继续参与组织救亡运动,许涤新受组织委派参加《新华日报》这一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的筹备工作。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许涤新作为首任编委会编委,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 远在江西的方卓芬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许涤新的文章,便去信与许涤新交流,二人经常书信往来。
1938年,方卓芬与好友一起去皖南参加新四军,成为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的一员。1939年,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作报告,对方卓芬等速记班学员的记录工作很满意,调方卓芬和吴博两人到南方局担任机要员,工作地点就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此时,《新华日报》临时编辑部也设在重庆,方卓芬和许涤新在重庆重逢。随着交往的增加,二人渐渐由好感产生爱意,确定了恋爱关系。
1939年9月25日,二人举办了婚宴,董必武、博古、王明、吴克坚等在重庆的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领导和同事都到场祝贺。当时许涤新与章汉夫合译的恩格斯的《论〈资本论〉》的稿费刚发到手,两人一人一半,许涤新正好有了婚宴请客的钱。

婚宴上博古笑着问许涤新:“你今天请了这么多客,要写多少万字?”许涤新回答说:“正好半本书的稿费。”博古便开起玩笑来:“这倒不错,半本书的稿费就讨了一个老婆!”一句话引得满堂大笑。
婚后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小名叫小火车,大名叫许嘉陵。1940年底,许涤新调到南方局担任董必武的秘书,同时作为中共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还兼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因工作劳累,许涤新坐牢时所患的肺结核病又犯了,时常咳血。
方卓芬因为照顾许涤新,很快便被传染。更不幸的是,他们的儿子“小火车”由于在4个月时曾摔了一跤,脊骨被摔坏,此时也被传染,患了脊椎结核。
当时正值国民党不断制造矛盾,斗争形势日益严峻。许涤新争分夺秒,在自身病情不断反复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此书一出版即热销,印刷达七次之多,直至被国民政府查禁。

许涤新又相继写出了《官僚资本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有力地开拓了我党在经济界的统战工作。
方卓芬全力照顾并协助许涤新开展工作,儿子小火车的治疗一拖再拖。1947年,小火车病情已非常严重,虽然做了手术,却落下了终身残疾,许涤新和方卓芬夫妇为此深深自责。
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离不开国防、经济等各条战线众多“战士”们的呕心沥血,他们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都值得国人铭记!
#历史人物##人物#
2015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2周年。这是毛主席生前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和吴桂贤在毛主席纪念堂,缅怀毛主席时拍的照片!
在70年代,谢静宜和吴桂贤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谢静宜从东北通讯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年,来到了中南海机要局,后来担任毛主席的机要员。还出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真的是风光无限。

吴桂贤原本是国营纺织厂女工,由于工作表现好,不但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还被送到大学深造,然后涉及仕途,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
到了晚年,谢静宜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住在平房里,老伴己去世,还要经受风湿病的疼痛。
吴桂贤退休后,热心做社会公益活动。
这次两个人重聚,既有重逢之喜,也有人生沧桑之叹!
#历史回眸#
在河北与北京交界的山区,住着一对与世隔绝27年的北大学霸夫妻。富豪同学前去看望,看到他们蓬头垢面的样子后直言:“你们要是缺钱,我给啊!”
王青松生在河南的一个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因为他从小过得很清苦,所以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凭借过人的能力,他高中毕业后不久,便成为了机要局的一名干部。
王青松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一直勤勤恳恳,业绩也十分突出。据说王青松一天五百个电话都能轻松记住,成为了当年的风云人物。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青松肯定是要参加考试的。于是在工作之余开启了备考之路,经过一年的努力,成功取得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本科毕业后,王青松又攻读了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后来直接被学校聘请为了教授,是学校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85年,国内出现“养生热”,王青松开始办起了养生讲座。
也就是在这年,王青松结识了自己的另一半——同样在北大任职的张梅。虽然两人相隔了12岁,但是通过王青松的讲座,两人相识、相知、相爱,一年后,水到渠成的步入了结婚的殿堂。
刚结婚的时候,小两口过得很滋润。除了本身的教师工作外,王青松的养生讲座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此时的王青松早已名誉双收,但他依旧没有放弃对学术上的追求:考博士。
不过就这此时,命运却跟王青松开起了玩笑。第一年,王青松的专业成绩和总成绩都名列前茅,但是却没有被学校录取。

时隔一年,王青松换了一个专业,又考出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再次被拒录。再加上当时养生热潮逐渐退去,王青松开始一蹶不振。
除了王青松以外,妻子张梅也遭遇到了事业的滑铁卢。张梅连续五年都没有评上讲师,可是明明张梅的专业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
生活的不如意,让小两口萌生了离开北大的想法。
1994年, 王青松在北京和河北交界处承包下2500亩地,想要一辈子隐居在这片大山里。
大概是过够了喧嚣的城市生活,王青松夫妇为这深山中的一口“新鲜空气” 一待就是27年。
深山没有电,没有网,甚至连人烟都没有。不过对于王青松夫妇来说,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也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多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小宇,山里条件艰苦到连儿子都是王青松自己接生的。小宇从小生活在原生态的环境里,学会了很多大自然交给他的知识,就算是家里的一百头羊,他放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可是转眼小宇七岁了,学龄的教育问题也成了他们的一个大的难题。虽然夫妻俩都是北大学霸,但是身为老师的他们很快意识到,单纯的家庭教育是有局限的。
而且小宇聪明好学,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为什么”涌上心头。渐渐地,他们心之所向的“世外桃源”成为禁锢孩子成长的一个“枷锁”。
其实小宇天资聪颖,一直跟着父母在封闭的环境成长确实很遗憾。
王青松夫妇觉得小孩子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虽然担心孩子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但还是觉得是时候走出大山了。
其实,王青松的一位富豪好友曾经来过这里拜访过他们。这位友人看到昔日意气风发的北大才子如今蓬头垢面落魄至此,顿时遗憾地嚎啕大哭,提出要资助他们。
当然,一生傲骨的王青松谢绝了这位友人的好意,但是考虑到小宇的成长,他们在2011年,还是恢复了与这位友人的联系。

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一切的一切让这对隐居夫妇不知所措。第一次接触网络的时候,王青松兴奋地表示:虽然对于自己很难,但是相信不出三年,自己一家定能重新适应社会。
有些人穷其一生,只为了走出大山,王青松夫妇看过世事繁华之后却选择逃离城市,回归大山27年。为了孩子再次走出大山。佩服他们的勇气,也很钦佩他们可以看尽繁华后,仍然能耐得住寂寞。
这是晚年的毛主席在张玉凤的陪护下到院子里散步的照片,拍摄时间是1970年。张王凤原本是牡丹江铁路局的一名乘务员,后被调铁道部专运处,出任首长专列的服务员。后来,又调往毛主席身边,长期担任毛主席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张玉凤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原因是,从1962年开始,张玉凤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文革"期间中国重大内外决策和毛主席晚年工作、生活的见证人。从工作岗位退休后,张玉凤深居简出,保持低调与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