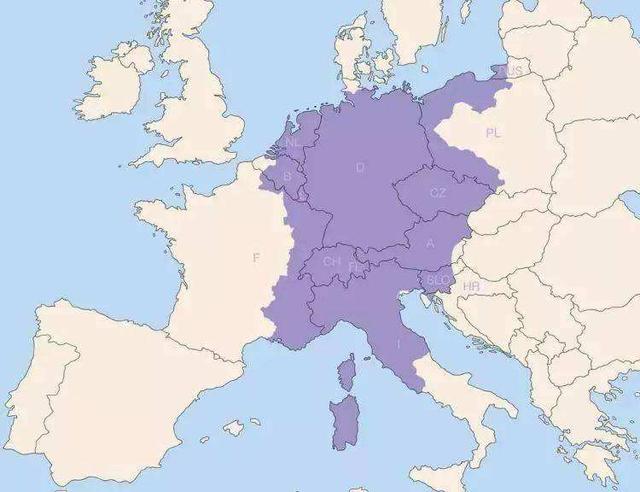居高观景,望远启智
口前地势狭,三山夹一盆,我登过北山看口前,也登过东山看口前。今天又登上了西山,再由西山远望口前。
远处山峦起伏,那就是东山和北山,在东山与北山的怀抱里,密密麻麻的楼群就是口前镇,说是口前镇,实际是永吉县城。
由于我并没有登到西山顶,脚下站的位置并不很高,并不能构成鸟瞰,见不到口前全貌。回头看看山顶,那里树木林立。即使登顶也未必尽看。
不过,这已经够劲儿了。除了几个高层大楼,其它的建筑都在我的脚下,向我俯首称臣。我哪有这样的资历,只因为我是站在西山之上。人不可以选择自己的个头,但可以选择自己的站位。
#湛江头条#今天出去晃海滩!眼望远去哪里?有大船大舰!那就是湛江港!码头工人日夜奔忙,为工人安心工作集团公司盖起了三十层工人宿舍楼!真亮点!我是农民工建设你们大楼工錢什么时候还?过了中秋又到年终?各层层互相报不见效!今湛江头条和你们商量!血汗钱!血汗钱!我们农民工!

踏莎行 . 忧思缕缕弦音诉
阴雨淋花,寒风戏露。
凭阑望远云烟舞。
抚笛轻奏念悠悠,
忧思缕缕弦音诉。
离雁零仃,浮萍孤苦。
天涯羁旅茫茫路。
高楼大厦笑寒门,
囊中羞涩街头住。
—— 今天的雨
今天的雨,没有雷电
虽然是夏至季节
下的正是江南烟雨,飘柔
有近望远,那边山头上
披上烟雨银纱,把山与天连接
这时,几只燕子飞穿在烟雨濛濛天空里
高楼大厦矗立在今天的烟雨中
街巷里来往着各种色样花色雨伞
今天的雨,对爱雨的人来说,刚好
付合他的心意,不用撑着雨伞
飘打脸上直接体验到雨丝的柔软,光滑
也可以尝到雨水的味道
是咸、是涩或是甜
这样也不会产生爱雨的人
言出互相矛盾

说爱雨,可是雨来了又用伞挡住
2021.06.24.
《迷茫的塔吊》
春节又近快过年
工地上的农民工,作鸟兽散
都回了老家
塔吊们眼巴巴地对望着,寒风中耸立
迷茫中不知跟谁诉说
中国的房产商不疯也不傻
却比疯子傻子更可怕
为啥造那么多房,卖给谁啊
问风,风只会呜呜呜地哭
问雨,雨只会扭秧歌
问雪,雪只会不断冷笑
问云,云却老是飘忽无语
只有一群鸟,好高骛远曾和他们打哈哈
暗示有多少空房被他们轻易占住
还嘲笑地鼠目光短浅
总喜欢抢占那些地下室
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这么无主的高楼大厦
却让白白地空着
问雷,雷却气得连连喊滚
干活的就该去干活,老老实实
闲事别多管,当心伤身
体贴的只有农民工,却全已走光

不管富人们有几套几十套几百套
反正塔吊也知道他们买不起房
有的人说,今年的欠着好多工钱
去年的老帐更要不上
辛苦的钱难挣更难要
光是有钱人之间玩的游戏,迟早也要玩完
但塔吊再迷茫的是跟铲车的关系
为啥闹得这么僵
过去很多时候,并肩作战
有如亲弟兄
好长时间,琴瑟和鸣
有如亲夫妇
如今为啥成仇敌,我日夜苦建
你却好端端地把它拆成堆,家业倾刻被毁
问谁问谁问谁
资本的无序扩涨,比塔吊们还要舞爪张牙
比挖机更加可恶嚣张
房价顶破天,还嫌不够高
楼盘如春笋,还嫌不够多
地球力无穷,也怕被压沉
土地爷被他们搞得千疮百孔,颜面丢尽
工薪族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难言幸福
还知道过年?总有一天
房产商们的日脚也要到头

现在你们过着年,我喝着西北风
但哪一天,你们这些贪吃蛇
总会连西北风都会没得喝
都说登高而望远,塔吊们却很迷茫
不知道将来何去何从
他们是否什么都看到了,还是什么也看不透
看透了,又能咋的
谁能听那些傻大个的铁疙瘩们,瞎胡扯
休休,这回去也
阳光大道你不走,偏向死胡同
难难,我塔吊废了可卖铁
但而可怜的农民工弟兄,你们一失业
何处讨生活
愁愁,这年头
今年且过,明年咋弄
莫莫,只要自己今天能过
莫管明天别人咋活
人人都这么想
人人也都这么过
否则,又能咋的
家住南关2胡同旧事2
(作者王洪恩)
下河洗澡(游泳),打朴腾的多(狗刨),也有YY浮的(仰泳),水性好的站在大南门桥上往下跳,眨眼工夫脑袋(头)就会从桥洞另一侧露出。孩子们都爱到河边玩,水流小的时候,光腚下水朴腾朴腾。上岸后身上指甲一划一道白不吝(化痕)。怕回家挨打找地方洗洗,再统一一下口径,路上分散走,相邀打手势,中指食指上下动弹,象极了自由泳的鞭腿动作。

沒有电视,收音机也少,固定时间的小喇叭也不是家家都有。下棋打牌也是很久以后。女孩子跳皮筋,踢毽子,盖房子,(地上划格,背身抛物,落在哪一格,回身蹦跳去找),男孩子们吃尤(地上划个锅放上杏核,手持铁链远远的往前抛冲消,沒了再兑),弹琉璃弹儿,拍画片,摔四角。最刺激的是找伴儿“打苏”,就地取材,木棍木板都行,一扎长(十公分左右)的小园棍两头削尖做苏,敲一头弹起,用棍板猛击,中途如对手沒按耍求投掷入锅(开局时地上画的方块)主动一方就耍变换方式,一手将书抛高,另一手将支屁股的棍(板)迅速抓起猛击下落的苏,耍准更要很还要看谁击的远。玩累了回家扒馍篮,逮住啥吃啥,也不耍菜可香了。大人看到最多吵(训斥)一顿,只要实话实说,给谁一起在哪玩嘞(的),很少‘挨打。
在南关地界有点名气的,除去已故的文老先生,就要数胡同西口的算卦盲人“邓仙儿”了,平日里打着卦板走街串巷,农闲时节,十里八乡,都有人大车来接,回来时满车新谷时蔬。新中国成立后成了监管对象。文革中多次被拉到百货大楼中间台阶批斗,腰缠玉米棒,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大蒜,搭链口袋装满小米黄豆。引来不少人观看。

白天挨批,私下里也不收手。我还领人到他家去过一次,天已很晚,老伴还在剥芋头给他吃,六十年代能吃上芋头沾白糖人家还真不多。一次户籍警摸到他屋里耍他给算上一卦,正算时老伴回屋,发现后忙喊“郭同志你怎么来了”,正解卦的邓老仙连忙收手,“不算了,不算了”一时传为笑谈。据说派出所还关过他几天。
胡同东口是菜市,西口是面点(粮站),南临百货大楼,遛湾(散步)吃嘴购物非常方便。老王家大(猪)肉火烧南关一绝,不出胡同就可闻到油脂混着大葱那浓郁的香味,高高的门台节上,经常有人等候,冬天挤满半个屋。刚出炉的火烧,滋滋冒油表层酥焦,一圈圈虼匝最是诱人,虽然拿着还烫手,也挡不住馋虫上窜。轻轻揭开,一点一点品味,那个香啊,闻着都醉。两毛一个,略有些贵,一般家庭一年也买不了几个,大众消费还是走街的小食摊。孩子们眼中的小奔脑(豆腐脑),大茶壶(油茶)乒乓擦(卖甜稀饭的)每天定时段在街上过。最喜欢老曹家的红豆稀饭,粘糊糊还有枣片,五分钱都盛一茶缸。据说用井伴凉水熬(煮),盛到底都不澥。一般人家孩子过生日,煮个鸡蛋在头上吿告(滚一下)。毛儿八分的就能过个生哦(eo)。

老邮电局北邻原是两层阁楼,打仗时被轰塌。解放后改成起脊平房。南面五间是糖杂公司合作社。经营油监酱醋咸菜,糕点罐头烟酒。最早时全天24小时营业,与日夜营业的糖杂公司车站门市部南北呼应,挑亮了南关的半爿夜景。
57年改名为糖杂公司回族门市部,南关的回民营业员都集中到这里,主任也是回民,糕点清真,与对面的三阳观一势儿(都是国营)。孩子们和这里的营业员混的烂熟。打酱油打醋都成了老主顾,大街上积水时往往会直接从后门进入,这边择菜那边去买也不耽误。
靠胡同口的五间门面,是水产公司在南关的唯一门市部。平时光顾的多是支援内地建设来的上海人以及驻汴部队的伙食单位。春节凭副食品小票定量供应带鱼,每到这个时候都要挨着胡同排起长队。每到卸车进货时候,总有邻居家孩子主动“帮忙”,中间会偷偷留下两蒲包。都说熟人多吃四两豆腐,街坊四邻很少排队倒是真的。合作社平时进货配备一辆后三轮,水产进货配备一辆前三轮,街坊邻居都经常借用,大多都是孩子们骑,骑车技术比大人都皮,不少人都是先会骑的三轮车,后会骑的自行车。
为方便过车,一号院门就成了胡同里唯一的单扇铁门,里边的门柱上方留一方孔,晚间上锁后手伸到里边可以打开,免得进货时敲门惊扰四邻。
胡同窄小过人确不少,西后街,柯家楼,四维街,陇海新村居民住户都从这里过,买菜购物办事逛街,一天到晚人来人往,零星不断。虽离大街有一段距离,闹中取静确很难做到。特别是那些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卖东西的小贩,叫卖声老远就听见,悠长圆润底气十足,满带乡音充满磁性。
“箍漏锅钉锅”…“焗锅焗盆”…“戗刀磨剪子”…“修理洋伞布伞换伞戗吧”…“打锡壶嘞嗬…”“有那麻绳头拿来卖吧,还有那生熟铁”…“换针换线收铺衬(旧布片)的来了”…“谁耍这老倭国(瓜)”…每每想起都会浑身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