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南昌军分区司令员邓克明亲率部队来到云山,对熊扬鹰匪部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进剿。参剿部队有南昌、九江2个军分区的6个连队和3个营属机炮分队以及永修、靖安、武宁的县区武装,剿匪部队集结了近千人。
熊扬鹰,永修县人,曾是国民党的文书、保长,先后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常备大队中队长、德安县保安大队长等职。他盘踞云山一带10多年,长期欺压百姓,实行血腥统治,群众称他为“云山王”。
江西解放前夕,熊扬鹰被封为“第二十一支队”支队长。他为了扩充实力,大肆搜罗国民党地方保安队、乡保队及旧军官、职员、地痞、流氓、地主恶霸等,拼凑起300余人,编成了4个大队,有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280余支,还有电台1部。
10月18日,剿匪部队开始进剿,随着战斗的深入,曾经不可一世的熊匪队伍一触即溃,解放大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熊扬鹰匪部打的是七零八落。见势不好,熊扬鹰仗着地理位置熟悉,带了20余名顽匪,逃出了包围圈。

10月30日,剿匪部队得到线报,熊扬鹰残余匪部,悄悄的潜回了真如寺。
真如寺,座落于云山以西的小盆地里,海拨800米高度,是有名的佛教圣地,有100多名和尚,太平年间香火不断。
通往真如寺,只有3条小路。一是自白石港西行穿过云山,是上山的主道;二是从戴家沿小溪右侧山林从南面进入;三是从北边江上经梅花坛、朱家岭穿过云山、五峰山两峰之间。这3条小路都是山高坡陡,有些地段是悬崖绝壁的险路,易守难攻。
11月5日,剿匪部队接到侦察员送来的情报后,连夜急行军25公里,次日凌晨包围了真如寺。十几分钟的激烈战斗,剿匪部队毙匪2人,俘虏匪兵十几人。但是很可惜,熊扬鹰因为去会相好而没有在寺内,所以再一次让他漏网了。
此时的匪首熊鹰洋,正躲在云山北侧梅家山山坳中的一个小茅屋里。这是他在云山的一个秘密窝点,他手下的大小头目和匪徒们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这里地处崇山峻岭的密林深处,没有道路,只能沿着山涧小溪攀缘而上,即使是砍柴打猎的村民,都轻易不会到这里来,更何况其他的人,确实是个避难的好地方。但是熊扬鹰仅仅在这里“安静”地躲过了5个昼夜,就迎来了他的末日。

剿匪部队为了尽快剿尽残匪,捉住匪首熊扬鹰,剿匪部队展开了分片搜剿,广大的群众也自发的组成一支支小分队,协同剿匪部队一起尽然搜剿,充当向导,使得整个云山地区,已经成为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
云山北麓何家坳、梅家山、朱家岭一带,分属九江军分区468团2营4连的搜剿责任区。11月10日这天上午,雨不停地下着,张连长和指导员的带领着4连早早地就吃过早饭,出发来到了梅家山,太阳刚刚上山,4连就已经搜过了好几个山头了。
略事休息,4连又向东面的高山前进,此时天公不作美,太阳不见了,还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百余米长的队伍在仅容得下一人的泥泞小路上,慢慢的向前挪动着。
队伍正在行进中,就听见“扑通”一声,有一个战士跌在石头上。腿都磕出血来了,可是这名战士不出一声,爬起来仍然跟随的队伍向前搜索着。

风雨不能阻挡住战士们的脚步,虽然雨水从战士们的帽沿上一串串往下流,风也刮得更紧了,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人掉队。
剿匪部队队穿过一片树林,转了一个弯,远处看见了一处山庄。剿匪部队慢慢的地逼近山庄,突击组长李大元带着2名组员走在最前头,3个人的眼睛瞪得老大。警惕的搜索着。
李大元对组员小声说:“注意前面的小房子!”两名组员,点点头,轻轻的“嗯”了一声,3人更加警惕地向前去。
就在离小屋还有五六米的时候,李大元从树林中观望,隐约发现小屋里居然有人在烧火,心里不禁一怔,自言自语说道:“咦,这可怪了,一个星期前来时还不见有人住,怎么回事?
“准备行动!”李大元小声说完,端起上着刺刀的三八步枪,二步并成两步,就冲了上去。与此同时,2个组员也从两边冲了上去。三人冲到小屋门前时,李大元一使眼色,一名组员一脚就踹开了屋门,“别动!"3人一齐端着枪,大喝着就冲了进去。屋中的2名土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三人制服。

然而此时屋门背后,还躲着的一名土匪,他突然跳出来,将李大元紧紧的抱住。
土匪抱住李大元后,就想从腰中掏枪,于是就松了一只手。李大元趁此机会,用劲把土匪一甩,结果就把土匪甩出了门外。这可正好中了土匪的下怀,他趁机一个打滚,就往树林里跑去。
“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李大元大声喝道。谁知那土匪那里肯听,只是头也不回地拼命的向树林中跑去。
李大元见状,就连忙追了出去。这个土匪显然是个惯匪,身手很敏捷,而且熟悉地形,三窜两蹦,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小黑点。
李大元一看,如果再不开枪的话,就快够不着了这个土匪了,如果让这个土匪脱逃出去,那么又将危害百姓!李大元三点成一线,食指一勾,土匪应声倒下。经当地村民辨认,此匪就是匪首熊扬鹰!他终究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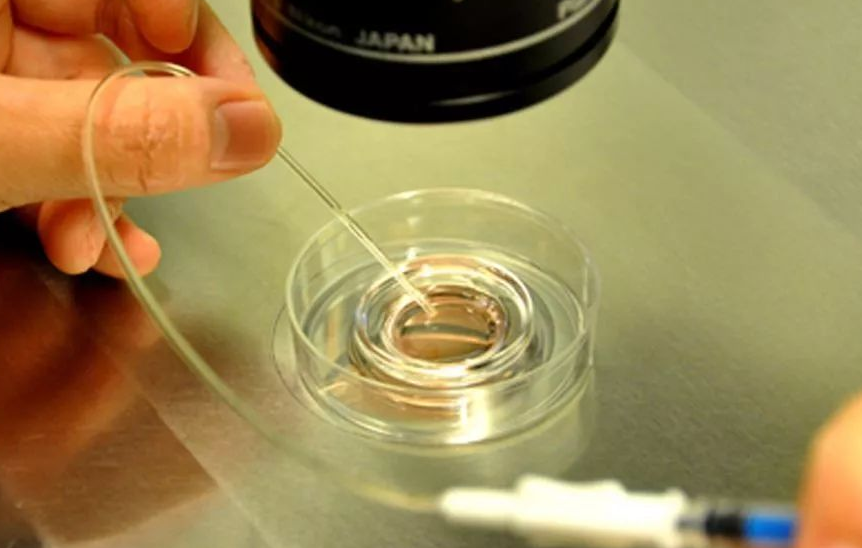
“江西武宁牵牛岭血案:无名男子惨死沟底,人命关天,警方踏破铁鞋擒捕真凶!”
第二回:书接上文。据死者家属反映,陶绍寓为了修房子,于四月二日晨经邻村陶学瑜介绍,身带一千零三十八元现金、一把黄油布伞、一个手提包、三条“双猫”牌香烟、一块“苏州”牌手表,进山买木料去了。据陶学瑜回忆:“三月初,我得知靖安县周坊综合厂代小辉要出卖一幢旧房子的木料,看货后,我决定买下来。由于没有出口证,当时未能成交。经商定,等代办好出口证以后发电报给我,然后再去取货交钱。四月一日,我收到代小辉发来的电报,要我速去办理买木料手续。由于我盖房子所需的木料已经备齐,就把这批木料转让给了陶绍寓,同时把代小辉发来的电报作为介绍信也交给了他。据说,第二天他就进山了……”
经调查,陶学瑜四月二日以后一直在家,不具备到牵牛岭作案的时间。侦察人员以山林调查组的身份赶到周坊公社,对代小辉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代是综合厂的负责人,他同该厂修钟表的王小鹤亲密无间。王的父母住在扬州公社,因此王平时经常过往牵牛岭。但四月二日至三日,代小辉、王小鹤都不具备杀人犯罪的时间,因此都排除了嫌疑。

周坊的几个可疑对象否定以后,侦察人员又第二次到昌邑公社。当地群众反映,良坪村的陶绪浩四月一日曾去过死者陶绍寓家,当时看到陶绍寓在数钱,四月二日早晨不知何故外出,四月五日才回来。经调查,陶绪浩二至五日在县血防站检查血吸虫病,因而否定了对他的嫌疑。
侦察人员在南昌县各公社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发现程统周嫌疑重大。一九八〇年初,一个自称程统周的人来大塘公社,听说当地张xx要买木料,诡称自己在乐化有8立方米木材要卖。张听说后随程一同前往,途中程又改口说,木料在杨家岭。张随程到了杨家岭,程指着粮管所的一堆木料说:“就是这堆,把钱给我。”张说要运回大塘以后才给钱,程见张不肯拿钱,就动手去抢,后发现张身上只有几角钱,这才撇开张溜之大吉。
对于这个行迹十分可疑的人,侦破组十分重视,根据该人熟悉乐化、杨家岭情况,立即赶到两地查询,很快在乐化砖瓦厂找到了程统周。同时在其住所发现了一个日记本,本内有武宁山区地形图及买木料的发票,还有一张在南昌县大塘公社招待所的住宿报销单。乐化砖瓦厂的工人反映说,程统周二日外出,六日才回来。大塘公社招待所服务员提供,五日晚上,程一脚泥巴匆匆来所。侦察人员据此分析:陶绍寓从昌邑到靖安县抄近路必经乐化,程既会骗术,又熟悉山区情况,是否在乐化与陶绍寓偶然相遇,将陶骗到牵牛岭杀害了呢?

经与程正面接触,他又支支吾吾,总是否认黑夜里去过南昌。于是就抓紧调查程统周的问题。但是,据永修县山角公社的群众证实:二日上午,看见程去其哥哥家,一连三天都没有出门,这就从时间上否定了程统周在牵牛岭杀人的可能性。后来查明,原来程统周打算在四月六日去大塘砖瓦厂做一笔投机倒把木材的交易,便于五日晚上摸黑赶到南昌。这就是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出真实去处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程统周的嫌疑又被否定了。
据调查了解,死者的行走路线是:四月二日早上从昌邑坐汽车,中午到达南昌,晚上住在奚雪礼家。四月三日早上六时三十分,从南昌乘汽车,上午九时到达靖安。
为了查清死者四月二日离家到遇害这段时间的详细行踪,进而发现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侦察人员分赴各地,先后找到四月二日早上昌邑至南昌,三日早上六点三十分南昌至靖安客车上的四十三名乘客。经过逐一调查,未发现可疑点。在牵牛岭附近查访的侦察人员也没有发现杀人凶手的踪迹。

侦察工作陷入僵局以后,侦破组及时召开了会议,再次分析案情,大家对零乱的线索,经过分析研究,终于理出了一点头绪!
死者四月三日九时乘汽车到了靖安已确定无疑。他的目的是去周坊买木料,为什么不去周坊找代小辉?是否被这一人以购买木料的名义骗到牵牛岭呢?如果死者受骗,其骗局应在靖安至周坊一带形成。根据周坊调查结果,未发现可疑迹象,于是把靖安县列为重点调查地区。侦察人员赶到靖安县,查遍了县城所有的客栈、旅馆。四月三日共有二千多张旅客登记卡,经过逐张审查,可疑卡片由五百张缩小到二十张、又从二十张缩小到靖安服务大楼一部的一张住宿发票存根上!这张发票存根引起了侦察人员的高度重视。死者是四月三日从靖安去周坊,这三人也同时离开靖安去武宁,时间、路线一致。这三人与侦察人员刻画的凶手很相似,必须尽快查清这三个人的情况……

待续第三回!
乡愁中的王家埠。
有些村庄和人一样,有记忆,比如我面前的王家埠村。
王家埠是江西省武宁县松溪镇的一个小村庄。它背靠雄伟的幕府山,面对碧波荡漾的庐山西海。青砖红瓦、白墙蓝檐的房屋错落有致,像一幅稀疏而独特的水墨画,美丽而温馨。在中国,像王家埠这样有姓氏的村庄太多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个村庄很普通。但正是这种共性,恰恰相反,让人感到亲切,似乎久别重逢,又回到了故乡。走在乡间小路上,看到炊烟袅袅,一抹乡愁情不自禁悄悄溢出脑海。
王家布虽然平凡,却承载着深刻的记忆,它的名字有一定的渊源。据《武宁县志》和《平阳族谱》记载,后晋兵部尚书王全因拒绝奉史景唐皇帝之命出使契丹,辞去太原之职,迁居江西德安。有一天,他骑着毛驴经过现在的王家埠时,毛驴突然卡住了,即使被鞭打。王全环顾四周,见拱门四周青山环绕,绿水潺潺,风水极佳,便决定搬到这里。当他来到这里时,他的后代兴旺起来,成为王兴的一个重要分支。后人称他定居的地方为绿竹坪。

从村里得知,这个地方不叫港,叫齐家庄,那里有八个姓齐的户口。他们田广地广,自高自大地说:“齐家有八大家族,不走其他家族的路,就上街县。”有一次,齐家娶了一个女人,这条路有一小段不是齐家的,所以他们用大米铺了路。为了表示自己不走另一条路,齐家如此奢侈。不仅如此,因为财政状况大,齐家平时也很显眼。有一次,他们真的移走了墓碑,把它铺在河边。齐家有一个叫王的长工,经常踩在上面,跳进河里玩水。有人嘲笑他:你只知道玩水,却看得出你是踩在祖屋的墓碑上。一翻身,苦力竟是王权的始祖。王兴人民向政府报告了此事,政府命令齐家安装墓碑。王冠的坟墓已经损坏。齐家随便埋了一个地方,安了墓碑。王家不在乎,他们每年都去祭拜。谁知道那个地方叫卧虎藏龙地,是风水宝地。从那以后,王家慢慢繁荣起来,但与他们结盟是非常不利的。每次王家牺牲,齐家的年轻人都会死很多。为此,齐家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收效甚微。最后,一家人搬出去了。王兴慢慢繁荣起来,成为这里的贵族家庭。

这个传说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确实反映了王家布人朴素的道德观念。那就是遵循正义的原则,善待他人,避免被上天谴责。我想正是遵循这种思想,王氏家族才日益兴旺。
王家布的记忆远不止于此。王氏家族兴盛后,并不安于现状。他们沿河出去,在河边建码头。人们称之为王家埠,逐渐成为村名。王氏一家勤劳朴实,出去挣了很多钱,回家盖房子。当时沿路都是王氏家族的高层建筑。王家港越来越繁荣,与永修土家港一样,成为修河的重要码头。1928年,民国创始人武宁人李烈钧主持修建了武宁第一条公路,这条公路起于永修土家埠,经王家埠沿何秀河到达修水。王家埠是这条公路的中转站,集水陆便利于一体,发展会更快。
王氏家族越来越兴旺,小小的王氏家族港口已经容纳不下日益兴旺的王兴后裔。有的移居武宁及周边县市的其他地方,有的外出谋生后定居在其他地方。如今,王权的后裔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江西的武宁、凤城,湖北的黄石、大冶、阳新、铜山。据初步统计,武宁县有几千人,而湖北有十几万人。

不幸的是,王家港并没有进一步繁荣。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来到了这里。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王家埠的高层建筑几乎被烧毁。遭受这场灾难,王家埠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柘林水库(今庐山西海)建成,王家埠一部分在库区,王兴人在库区聚居,搬到了对面的金口村。之后,一些来自浙江、河南、安徽的移民以及县内其他地方的人陆续来到这里定居,王家埠成了杂姓聚居的村落。虽然也有姓王的人,但都是后来才迁的,并没有真正的皇权传人。王家布真的成了记忆。
虽然他们住在不同的姓氏,但人们仍然称之为王家埠,他们仍然坚持着村庄的传统。当你来到这个村庄时,你可以到处听到关于王兴的故事和传说。像王氏家族一样,他们遵循正义的原则,善待他人,勤劳节俭,努力进步。这个村庄非常鹭港,人们非常快乐。近年来,当地政府下大力气把这个地方建设成新农村的中心,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王氏一家迁居外地后,仍视其为故乡。几千年后,皇权的坟墓依然静静地躺在“卧虎藏龙之地”。每年都有很多皇权后裔来到这里寻根问祖。他们把这个村子的记忆代代相传给了后代,成为了这个家庭共同的记忆。我想:他们来这里寻根的时候,面对没有皇亲国戚后裔的王家部,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感到欣慰;也许,他们非常怀念祖先耕种的这片土地...他们离开王家埠会一次次回头吗?我不知道。其实不仅仅是王兴人,还有王家布。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旦离开家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突然发现,原来温暖温暖的乡村不知不觉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家乡只能在远处看到,却很难到达。有人说,人生的终点是流浪,故乡是乡愁聚集的地方。因为西海的建设,当年的码头早已沉入海底。王家布在不断变化。一成不变的,是凝聚在村民里的深刻记忆,是浸淫在山川里的浅浅乡愁...#情感#

1998 年, 为了参加湘南起义 70 周年纪念活动, 91 岁高龄的萧克回到家乡嘉禾县小街田村, 这是他继 1981 年首次返乡之后第三次回来。
看到村里孩子上学难, 他就多方牵线搭桥, 促成 3 位香港实业家捐资 25 万元建成了小街田希望小学。
同时, 为了给孩子们增添精神食粮, 萧克还向县图书馆捐赠了万余册图书, 整整摆满了五六个大书架, 县图书馆为此专门设立了“萧克捐书专藏室”。
“离家半纪经百战, 至今耄耋始还乡。全村老小倾家出, 季子归来无锦裳。”
这首名为《还乡吟》的诗是 1981 年12 月, 萧克离家 54 年后第一次回家乡时所作。
那次, 萧克让司机在村口停车,自己摘下帽子, 步行进村, 他深情地说:“我是回家, 不是来视察, 是一个人民的儿子回故乡。”
一边走, 萧克还一边指着路边的房子辨认那是谁家, 虽然已分别半个多世纪了, 可他依然对每一家记得清清楚楚。

看到前来迎接的村民, 萧克用乡音大声打招呼: “你们好, 大家都好哇! ”
他还特意走到村里的水井旁看了看井, 说: “这样的井, 水不行, 要改造。”
1988 年, 老人第二次回来时, 还召集村民在一块空地上开了个会, 号召大家:“要勤劳, 把事情做好, 地种好……”
萧克关心家乡子弟的成长, 关心家乡的发展, 但对自己的亲属, 却要求十分严格。
第二次回家乡时, 萧克和亲属们围坐在一起吃中饭, 桌上的菜只有酸青菜,主食是南瓜稀饭, 可萧克还是勉励亲属说: “在下面好好做, 虽然很辛苦, 但有饭吃。”
有一年, 一个侄儿的孙女想当兵, 体检时个头矮了一点儿, 他们抱着一丝希望找到萧克那儿, 萧克的儿子知道后说,老爷子是不会让走后门儿的, 我们不能坏了规矩。
严格要求亲属, 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这是萧克行事的一个原则。其实,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 萧克本人就是一个遵守组织纪律、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的典范。

1955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时年授上将军衔 55 人, 1956 年和1958 年各补授 1 人。
前 10 名上将名序排列依次是: 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
虽然萧克名列第一, 但无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 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萧克担任过的职务却不逊于任何一员大将。
当时很多人认为按照萧克的资历和功勋授予上将军衔是委屈他了, 为他抱不平。
萧克对此却很坦然, 他说: “很多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战争中都牺牲了, 我早该打死了, 评不评衔, 评什么都行。”
并随兴谈起了一段古人佳话: 东汉大将冯异是光武帝时期的开国大将, 战场上, 勇不可挡, 功勋卓著,但他为人谦和, 每到将军们聚会论功时,他都会躲到一旁的大树下, 从不参与争论, 由此东汉军中都称他为“大树将军”,我们共产党人, 难道还不如古人吗? 萧克宽广的胸怀和高风亮节,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克组织观念非常强, 一直被熟知他的人传为美谈。由于需要, 萧克曾多次被调动工作, 从无怨言。
1936 年 9 月, 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萧克代替生病的王树声出任三十一军军长, 攻打胡宗南部。10月 20 日, 红军长征结束 4 天后, 萧克正式赴任。
有人背后议论“这个萧克不动脑筋, 他们六军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放着副总指挥不当, 去当军长”。
萧克对此毫不理睬。至此, 萧克成为极少数在红军三大主力的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开始后, 萧克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 在八路军师级以上的高级将领中, 他依然是最年轻的。
后来, 他又调任挺进军司令, 实际上麾下没有多少兵马, 可他照样欣然接受,干得有滋有味。
1958 年,萧克调任农垦部副部长。
1968 年 萧克再次被隔离审查。
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被安排去江西永修得“五七”干校“。

永修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山里的冬天特别潮湿阴冷, 冻得实在受不了, 萧克就用跑步、劈柴等方法来取暖。尽管萧克身处逆境, 但他那重原则的个性一点也没变。#开国将帅#
当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他调查核实有关材料, 他总是实事求是地有啥说啥。
当地山民主动与他聊天拉家常, 孩子们也很喜欢他, 要他抽空讲红军和长征的故事。
1972 年 1 月 16 日, 组织上通知萧克回北京工作。临走时, 他将自己在“五七”干校当木匠、油漆匠时做的凳子、桌子甚至笨重的木工凳都带了回去, 一直舍不得扔掉。
他常说那是他在江西那段特殊岁月里的一个永久纪念。此后, 云山垦殖场的干部群众还经常到北京去看望他, 找他叙叙旧。他曾对门卫说, 只要是江西的人来找我, 就马上通知我。“我早已经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每当谈起江西, 萧克总是感慨万千地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