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上玄奘法师的前世】,今天小编给您分享一下,如果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关注本站哦。
- 内容导航:
- 1、历史上玄奘法师的前世:还原真实的玄奘法师,国人不该遗忘“千古第一人”
- 2、历史上玄奘法师的前世,大唐第一高僧玄奘法师
1、历史上玄奘法师的前世:还原真实的玄奘法师,国人不该遗忘“千古第一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第10章
锦江缘
走出大山,一行人终于来到一座人烟稠密的城市。
此城地处群山之中,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环绕山间,空气中始终萦绕着一股甜甜的蜜香。街道上店铺林立,车水马龙,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丰饶平静,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

长捷拉住一位匆匆赶路的行人问道:“请问这位檀越,此地可是益州吗?”
“是啊。”那人看看长捷,又看看另外三位僧人,“这里是益州首府成都,四位师父也是去听道因法师讲经的吗?”
一听道因法师的名号,景法师不由得面露喜色,合掌宣了一声佛号。
长捷又问:“请问檀越,道因法师在何处讲经?”
“就在城东的多宝寺。”那人往前一指,“我正是要赶往那里去听经的。这些日子法师在多宝寺里开讲《维摩诘经》,听者上千人!我得赶紧走了,去晚了只能坐在后面,就听不清了。”
说罢施了个礼,匆匆而去。
慧景法师心中欢喜,对玄奘道:“老僧早说过你这孩子有佛护佑,果然不虚。道因法师乃是声名久播之大德,其人精博勤敏,为道俗所共尊。就连一向倨傲的暹公读了他的论文,也不禁肃然改容。这《维摩诘经》你在洛阳虽已学过,却也不妨再去听听道因法师所讲。”

听了这话,玄奘自是欢喜从命。四人便齐往多宝寺去挂单。
多宝寺是益州法筵最盛的寺院,长安、洛阳等地高僧大多驻锡于此。除道因、宝暹外,道基、道振法师也在此寺讲说经论。
从四面八方投奔益州的僧人,挂单于此寺者不下千人,后来者想挂上单很是不易。好在景、空二法师本来就是东都名高德昭的大德,而长捷、玄奘兄弟也有一定名气,就连宝暹、道基这样的大德高僧都对他们兄弟有所耳闻,如今见这四人前来,自是分外高兴,忙将他们迎入寺中。
成都位于“天府之国”的腹地,碧绿的锦江如一条玉带般环绕着这片土地,浇灌出一望无际的平畴沃野。
锦江江水澄澈,水底的石子和游鱼清晰可见。远处石桥两侧石缝中的青草,温婉地依附着青石板,就连点缀其间的细小花朵都能数出数来。
江边石阶上,几名少年女子一边说笑一边濯锦,偶尔打闹起来,间或爆发出一阵欢笑。

此情此景令人着迷,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战乱之地的关中人来说,这种久违了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伴随着濯锦女子绵软轻柔的笑语声飘荡在锦江之上,一直软到心里去。
“咱们蜀中所出的锦缎,质地精良,花样繁多,闻名天下。”一位年轻居士站在江边,对玄奘说。话语间充满了自豪之意。
“在咱们这里,织造锦缎的作坊叫‘锦院’,织工聚居的地区叫‘锦里’,濯洗锦缎的江水叫‘锦江’,甚至整个成都也叫‘锦城’。”
多美的名字啊!玄奘想,“锦院”“锦里”“锦江”“锦城”,这些名称触动了他心底最柔软的那根琴弦——那个同样以“锦”字为名的女孩子当会喜欢上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吧?希望这个美丽的地方能够带给她幸福和快乐!
或许真如景法师所说,“魔由心生”,没过几天,玄奘就在多宝寺的大殿上再次见到了前来上香的锦儿。

她看上去消瘦了很多,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里竟闪着几分忧郁的光。
“想是长途跋涉,太累了吧。”玄奘心里想着,又不想多生事端,因而便没有打招呼,只悄悄地走开了。
蜀中是个好地方,这里风光绝美,气候温暖、瓜果遍地。施主们大都性格温和,开朗率性,无忧无虑。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已是天下文士向往之都——在如今这样的乱世,处处饿殍遍野,唯蜀地例外,于是,各地僧侣名士纷至沓来。
众多高僧大德在成都大开讲席,传授佛经,使得这座城市俨然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
玄奘自然不会放过向诸大德请教的机会,他不仅在多宝寺拜师问疑,还在益州各丛林寺院往来听经,除继续研究早已流行的毗昙、涅槃、摄论之学,还研究新兴的法相唯识学。
他本就悟性非凡,又好学深思,很快便在巴蜀佛教界崭露头角。开坛授业的高僧大德们无不对这个少年沙弥交口称赞,同席僧侣更是被他深深折服,并推举他登坛讲经。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玄奘年满二十岁,依佛制可以受具足戒了。
所谓具足戒,就是圆满完全的戒,这是佛教中的最高戒律。欲受戒者必须是年满二十岁且品行端正的沙弥,由十名以上高僧进行举荐,方可受戒。
这些限制对玄奘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几乎所有在蜀高僧都对这个年轻人印象深刻。这些高僧中,宝暹法师以讲授《摄大乘论》久负盛名;道基法师则对《杂阿毗昙心论》深有研究;还有一位道振法师,是研究《阿毗昙八犍度论》及《迦延》的专家。玄奘都曾一一拜师求学,以至于几位法师坐在一起讨论受戒人选时,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
“那孩子是真正的佛子。”慧景法师道,“从洛阳到成都,老衲主持各种法会无数,法会上的僧众常有上千,在一起讨论佛学,辩经问难时,玄奘总是最为出众的一个。”

“景师所言不虚。”道振法师点头道,“蜀地居士都爱听他讲经,很多同修视他为汉代的清流李膺、郭泰。”
“玄奘的才学只怕犹在李、郭之上。”道基法师沉吟道,“老衲数十年来常游于四方讲肆,却从未见过有哪个少年如他这般神悟的!”
宝暹法师也点头附和,他原本是东都四大德之一,多年前因杨玄感叛乱而受到牵连,被流放到蜀中,吃了不少苦,因而脾气显得有些古怪。很多晚辈僧侣都不愿意亲近他,难得的是,他竟与玄奘颇为投缘。
事实上,在蜀中的年轻僧侣中,很多人喜欢景法师的清新,而认为暹法师过于高傲古怪,不自觉地加以贬抑;但是也有一些弟子服膺于暹法师的高论,认为景法师讲的《摄论》过于平淡细致,时时报以冷嘲热讽。而玄奘却是两家并听并学,对两位法师都极为尊敬,且能将两家学说融会贯通,因而深得二位法师的称许。

就在法师们讨论受戒人选之时,玄奘正在多宝寺山门前的广场上讲经说法。偌大的空地上挤满了前来听经的僧人俗众。
讲经结束后,居士们照例围上前来问东问西,玄奘则一一为他们耐心解答。
突然,他感觉有人用力拉扯了他一把:“嘿,小和尚!”
玄奘吃了一惊,近些年来他声名日隆,已经很久没人敢对他这般无礼了。
定睛细看,眼前竟是一张颇为熟悉的英俊面庞,那笑容既阳光又有几分慵懒,一身天蓝色儒袍,潇潇洒洒——竟是多年未见的叶丹参!
“阿弥陀佛,原来是叶小居士!”
此时的玄奘已不同于年少之时,乍见故人,心中自然欢喜,语气却还是冲和平淡。
“嘿嘿,多年不见,小和尚果然了得啊!”丹参嬉笑道,“我在底下听经时,已经能感受到你头顶上有佛光闪耀了!”
“是啊,确是多年不见了。”玄奘感叹道,“不过居士倒是一点儿都没变,还是那么喜欢开玩笑。”

回到寮舍,丹参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
乱离之世,颠沛流离,自然有许多的辛酸往事。好在丹参生性乐观开朗,那些往事到了他的嘴里,竟然全都成了可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了。
“令尊的身体还好吧?”玄奘终于找机会插了一句嘴。
“好!好得很!”丹参兴奋地说道,“昨天他还念叨你呢。”
听了这话,玄奘心中不禁泛起思念的情愫,他感慨地说道:“叶先生当真是君子菩萨,记得在长安时,玄奘使用先生传授的医方配药,治好了很多灾民的病。那段日子,庄严寺里聚集了那么多人,却没有爆发瘟疫,全赖先生的功德。这一次,玄奘定要登门拜望。”
“好哇!”丹参喜道,“父亲一直惦记着你,他常说教你是最划算的事了,上回多亏你救命呢。前些日子我们刚到成都时,听这里的居士们说起玄奘法师如何如何。父亲忍不住跟他们说:‘你们说的那个玄奘法师啊,那是我的徒弟!’人家不信,说他吹牛,弄得他好没面子。你要是去看望他,他定会欢喜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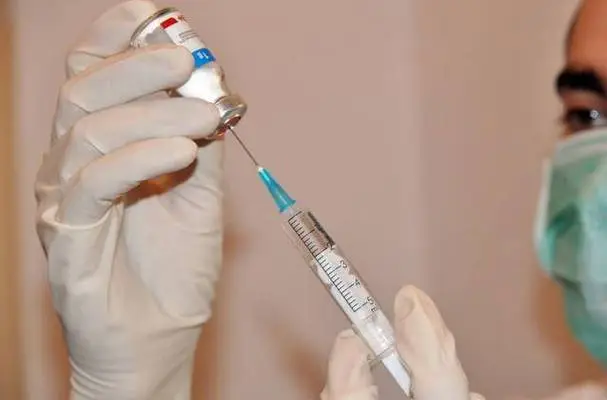
丹参所说的“救命”一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还是在洛阳的时候,叶先生突然得了急病,自己开了药方,居然越吃越糟,直至起不了床。
“唉,医不自医啊。”先生躺在榻上,叹息着想。
这是中医里的一句话,很奇怪——有时候医生自己得了病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原本很好用的方子用在自己身上,却不灵了。
为什么会这样?依照民间的说法,医生们其实都是在逆天而行。本来人得了病就应该死的,医生非要给治活了,所以会得罪阎王爷,让你自己生奇怪的病。
玄奘惊讶于很多人会相信这等无稽之谈,他说:“这世间既然有医术,有草药,那也就意味着这是上天给人留下的一条活命之路,畜牲不舒服了尚且知道主动找草药吃,人治病怎么能算是逆天而行呢?”
然而那一次叶先生确实病得不轻,一向对背医书不感冒的丹参也着急起来,跑到净土寺,将玄奘请到了父亲的榻前。

搭过脉后,玄奘神色轻松,只开了一味药:用甘草泡茶。
“这样就行吗?”丹参有些不信,甘草实在是太普通的药物了。
“相信玄奘,应该没问题。”玄奘回望了一眼病榻上的先生,微微一笑道。
果然,几天后,叶先生的病渐渐好了起来。
事后,玄奘对丹参解释说:“先生不是病,是中毒了。”
“什么?中毒?!”丹参大吃一惊!
“居士不用紧张。”玄奘安抚他道,“叶先生是有德医师,每次配了新药总是自己先品尝一下。然而是药三分毒,天长日久,腹中积药太多,身体自然会出问题。用甘草泡茶,可解百药之毒。”
“原来如此。”丹参这才恍然大悟。
对这个勤奋聪悟的少年僧侣,叶先生本就十分喜爱,这次又亏他救命,更觉得是前世的缘法。既然丹参不喜学医,叶先生便索性收了玄奘做学生,悉心教授医术、针灸,而玄奘对这位医师,也是越来越敬重。在他看来,有济世之心的医师,行的都是菩萨道。

玄奘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丹参却已换了个话题:“小和尚你知道吗?这些日子,父亲正在家中预备聘礼,打算要去替我求亲呢。噢,对了,我们提的那家姑娘你是认得的。”
“是吗?”玄奘也替他高兴,“那沙门要先恭喜居士了。”
丹参奇怪地看着他:“我说那个姑娘你认识,你就不想问问她是谁吗?”
“玄奘不必问,居士若是愿意说,自己便会说的。”
丹参呻吟一声倒在了床上。
“好吧,我跟你说。”丹参今天看起来心情格外的好,直起身子说道,“还记得锦儿吗?”
玄奘一怔:“林先生的女儿?”
“不错,就是她!”丹参兴奋地说道,“来成都也有不少时日了,前些日子才见到她。真是女大十八变啊!小和尚你不知道,现在的她真是美极了,跟小时候完全没法比!”
我没觉得她有什么变样啊,玄奘想,只不过你小时候不曾注意罢了。

丹参可不知道玄奘在想什么,自顾自地往下说:“我一回家就跟父亲说,我要娶她,我非娶她不可!父亲听了很高兴,说我长大了……”
“等等……”玄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居士前些天才见到她,你确定她肯嫁给你吗?”
“为什么不肯?”丹参显然很自信,“我们打小时候起就是好朋友。”
“可玄奘记得那时候,你还嫌她烦呢。”
“那是小孩子家不懂事,当不得真的。”丹参一摆手道。
突然又觉得有些心虚:“也是啊……小和尚,要不,你帮我们念念经怎么样?求佛陀保佑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玄奘觉得好笑:“沙门自然可以帮你。不过,居士若是有诚意,最好自己念。”
“对对对,是该自己念的。”丹参托着下巴,认真地想着,“哎,你说我念什么经好呢?”
送走丹参后,正好碰上要回寮舍的长捷兄长,见面就说:“恭喜四弟要受大戒了,沙弥只有受具足戒后才可成为真正的比丘。”

玄奘趁机向兄长请教有关具足戒的问题,长捷一一回答,又说道,“比丘的戒律有二百五十条,受戒之后,可够你学一阵子的了。”
“这么多?”玄奘有些惊讶,“为何以前从未听二哥说起此事呢?”
“佛制比丘戒是不可对沙弥和居士说的。”长捷解释道,“这些戒律极为烦琐,受戒者需历五夏专门研习方可通达。沙弥居士若只是随便看看,很容易断章取义,用僵硬的框架来看待比丘。说不定还会因此造下口业,惹出麻烦。再说,沙弥居士也没必要知道这些,修行人只需守好自己的戒律,管好自己的身口意就可以了。”
“可是,比丘戒又为何要制定得如此烦琐呢?”玄奘心中颇为不解。
在城南空慧寺的长廊下,道基法师对玄奘解释道:“比丘戒条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要僧众借由戒律的规范,养成足堪住持佛法,成为人天师范的僧格,使正法得以久住。故而佛陀所制定的戒条内容,包括比丘们对一己道德的提升,对教团应负的责任以及微细的威仪行止等,种类繁多,粗略可分八类,即波罗夷、僧伽婆师沙、不定、舍堕、单堕、波罗提提舍尼、众学、灭诤,计有数百条。”

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原本是东晋慧远之弟慧持入蜀所建的“金渊精舍”,又名“龙渊寺”,近些年为避唐王李渊之讳而更名为“空慧寺”。
玄奘之所以从多宝寺移居到这座著名的寺院,暂时结束了有系统的全面从师受学,是因为他要在这里坐禅读经,调适身心,准备受戒。而道基法师正是他受戒的教授师。
“这些戒条在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吗?”玄奘边走边问道。
“是的。”法师答道,“佛陀成道后的最初十二年内,并未给僧团制定任何戒条,只是随机宣讲他所证悟到的佛法,根利之人即闻即悟,当下就能心与道合,达到断恶修善利益众生的目的,因而也就能够迅速获得解脱。
“然而十二年后,随着佛法的广泛弘传,出家人越来越多,僧侣中就不免龙蛇混杂,凡圣同居了。有人出现了违背修道精神的行为,于是佛陀便因事制戒,告诫弟子们‘以戒为师’。对了,玄奘,你可知为何要选择在这空慧寺里举行受戒仪式吗?”

“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慧持法师的栖止之地吧。”玄奘答道。
道基法师点了点头:“很多人都知道在庐山结社念佛一心想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慧远法师,却不知其弟慧持大师也是龙天师表。他们兄弟二人都曾师从于东晋的道安法师。”
玄奘恍然大悟:“道安法师乃是东晋名僧佛图澄的大弟子,是第一位为中原佛寺制定戒规的人。”
“不错。”道基点头道,“慧持大师一生精严持戒,从无懈怠之时。晋安帝义熙八年,大师对弟子们说:持戒犹如踩在平坦的大地上,各种善事善因才可能由此生长,你们无论是行、住、坐、卧,都应该严谨奉行。言罢坐化,春秋八十六岁。”
玄奘合掌道:“多谢师尊慈悲开释,弟子明白了。”
来到叶家,一股熟悉而又亲切的药草味儿扑鼻而来,熏得玄奘都要醉了。
“这次决定来蜀中,可真是来对了!”看到玄奘,叶先生满面红光,兴奋地招呼道,“你来看看这是什么。”说罢递过来一株翠绿的小苗。

玄奘接过看了看,道:“这是枸杞。”
“想不到吧?”叶先生笑道,“这东西在咱关中是宝贝,平常难得一见,这里却满山都是!你再看看这个。”
他又递过来一株看上去颇为奇特的植物。
“这是何物?”玄奘惊讶地问道,“玄奘来蜀地已有三载,竟然从未见过这种草。”
“没见过?”叶先生立即得意起来,“这叫作‘七叶一枝花’!原本生长在楚地,蜀中确实是不多见的。楚人都说,此物治痈疽便如用手拿一样!我在山上转了好几天才发现了几株。”
听了这话,玄奘不禁大为感动:“先生真乃良医也!却需注意身体,莫要独自进入山林。”
“无妨!”叶先生笑道,“我这副身板还好着呢,还能看着孙子长大!”
说到这里他颇有意味地看了看玄奘,爽朗地说道:“孩子,还俗吧!等我给你和林家姑娘红红火火地办上一场婚事,再给丹参说上一门好亲事。然后,咱爷儿几个就一块儿行医济世!”

玄奘大吃一惊:“叶先生……您……您说什么?”
“别不好意思了。”叶先生呵呵一笑道,“我都知道了!林家姑娘喜欢你,这没什么。所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嘛,再说还俗娶亲的僧人多着呢,只要真心真意,想来佛祖也不会怪罪。对了,你不用在乎丹参,他也就是小孩子家心血来潮。等这事过去,我再请人给他说上一个漂亮姑娘,他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玄奘越听越晕,不明白叶先生何以突然冒出这样一番话来。
他小心翼翼地说道:“叶先生,玄奘相信您是一片好意。只是,玄奘自幼出家,虔心向佛,从未起过还俗之心。况且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受具足戒了,先生这时候提还俗娶妻之事,莫不是在拿玄奘开玩笑吗?”
听了此言,叶先生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原来,自打丹参随父到林家参拜林居士时见到锦儿,就被她所倾倒。得知十七岁的锦儿依然待字闺中,丹参更是欣喜若狂,回到家中就对父亲说,此生定要娶她为妻方可。

叶家与林家原本就是世交,丹参想娶林家姑娘,这对叶先生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立即备下聘礼,向林家正式求亲。本以为林家定然也会顺水推舟,玉成这桩美事,谁知林先生却是一脸的唉声叹气。
理由无他,林家小姐不愿意嫁人,逼急了,就以出家为尼相威胁。
两位父亲谁也不知这姑娘犯了什么邪,倒是母亲了解闺中女儿的心思,她告诉丈夫,锦儿已经心有所属,她喜欢的竟是那个少年法师玄奘。
林居士顿时大怒,这等既得罪佛祖又耽误女儿的事情,不是胡闹吗?
而叶先生却有些误会了,尤其是听林夫人说起在汉川之事时,便误以为两个年轻人已暗中相恋多年,只不过慑于戒律而不敢说出口罢了。
“我早说过陈祎不该出家的。”叶先生心想,“少年人就是面皮嫩,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呢?僧人还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他还只是个沙弥,并非受过大戒的比丘。”

他一来生性坦荡,二来对玄奘本就十分偏爱,三来又觉得自己的儿子与锦儿已经多年未见,就那一面之缘实在无法与人家的两情相悦相比,若是勉强娶来,人家女娃娃成天价郁郁不乐,自己的儿子又能有多开心?倒不如索性成全了那对有情人,也是一桩美事。
这样一想,当即爽快地说道:“二位不必为此烦心,此事包在老夫身上!”
说罢,大笑着出门而去。
可是如今看来,玄奘压根儿就没有还俗娶妻之意。叶先生这才明白过味儿来,敢情这林家女娃同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样,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嘛。
这样想来,叶先生竟又觉得,丹参和锦儿才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玄奘刚回到空慧寺,迎面就碰到了锦儿,看来,她已在此守候多时了。
“我想出家!”少女红着眼圈儿,直截了当地说道。
玄奘心中暗暗叹气——我的心魔真有这么强吗?

他斟酌着对锦儿说道:“出家是件大事,岂能凭一时的意气行事?这样就算出了家,道心也不会坚固的。”
“我不管!”锦儿执拗地说道,“你道心坚固,我怎么就不坚固了?你瞧不起人啊!”
玄奘被噎了一下,但他想,这女孩儿明显不是真心想出家,自己还是尽量劝她回头的好。
当下耐着性子劝道:“施主,出家也须随缘,强求不得。你若果真与佛有缘,自然会有结果的。”
“那你出家是随缘吗?”锦儿不客气地反问道,“你敢说这不是你硬要做的选择?你真的一点儿都没有攀缘吗?”
听了这话,玄奘一时竟无话可说。
他不想为此多生事端,只得点头道:“好吧,檀越若真想出家,成都倒是有几间女众寺庵,你可以去那里问问,看看朝廷何时下发度牒。”
往前走出几步后,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身后一脸愕然的锦儿道:“若果真出家了,就好好修行吧。”

说罢转身离去,再也没有回头。
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锦儿不禁泪流满面,伤心地啜泣起来……
玄奘走到大殿门口,却见景法师正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开弓没有回头箭。”老法师徐徐地说道,“玄奘,你真的决定领受具足戒吗?”
“这是弟子多年的夙愿。”玄奘平静地回答道。
“善哉……”长老垂目合掌,不再多说。
寂静的夜晚,一盏灯火,在古老的禅房内静静燃烧,室内飘荡着一股淡淡的檀香气。
玄奘独自静坐在蒲团上,从暮色初起到现在,他已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个时辰,却发觉自己怎么也定不下心来,锦儿那双晶亮的泪眼时不时地在他眼前晃动,晃得他心烦意乱,难以安定。
“阿弥陀佛。”他对自己说道,“魔由心生,亦由心灭……”
可是要灭魔并非易事,山寺的夜晚静得可以听到烛火晃动的声音,至于那不平静的心跳声更是挡都挡不住了。

既然无法入定,那就干脆诵经吧。
打开面前的经卷,读了一会儿,依然无法平静,只觉得心海之中云起鸟腾,风动尘起,这虚幻的生命竟是如此喧闹。
玄奘极力收拢着纷乱的心思,喃喃自语:“念起即觉,不动不随……”
经书也看不下去了,他索性起身离座,来到窗前。
这才发觉,窗外的天空不知何时已飘满了蒙蒙细雨,暮春的雨丝看上去诡秘而美丽,那有节奏的“沙沙”声就像佛祖慈悲的开示……
“你这小和尚!”门“咣当”一声被撞开,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打断了玄奘的沉思,不用回头,他也知道是谁冲进来了。
“平常口口声声说什么慈悲为怀,却原来都是假惺惺的!对一个女孩子也如此残忍!”丹参气愤难当,连声音都有些变了。
玄奘回过头来:“我如何残忍?”
“锦儿一个花朵般的女孩子,你却要她出家为尼,这难道不是残忍吗?”

玄奘摇了摇头:“居士你搞错了,第一,玄奘从未要她出家,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第二,出家是件功德事,如若真是她本人自愿,此事对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本人自愿?”丹参气极道,“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她这么做的用意!你居然忍心这般堵她的话!你,你……你真是太残忍了!”
“居士。”玄奘有些奇怪地看着他,“你不是早就跟我说过,想要娶她为妻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丹参一屁股坐了下来,端起案上的茶碗就喝,“因为我喜欢她。可这是我自己的感情,与她无关!我知道她喜欢的是你,这没什么,只要她开心,我怎么样都行!”
玄奘心里升起一种感动:“阿弥陀佛,居士一片真心,上天都会感动的,她又岂会不明白?玄奘觉得,你们两个才是真的有缘。”
“你拉倒吧!”丹参对番话毫不领情,不屑地说道,“说什么随缘啊?她喜欢你,这难道不是缘?她对你的爱,难道上天就不会被感动?你为什么要抛下爱你的女孩子独自一人念经参禅悠闲自在?这是随缘吗?”

“我与她并没有缘。”玄奘平静地解释道,“如果我们两个真有缘的话,我也会喜欢上她的,我会为了她不顾一切地还俗,那样才是缘。”
“你没有爱上她,是因为你的脑筋出了问题!”丹参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就是不明白,这和尚有什么好当的?倘若全世界的人都出家当了和尚,人人都没了子嗣,这人类世界岂不是要灭亡了?”
“你会去当和尚吗?”玄奘反问道。
“我?当然不会!我想都不会想!”丹参愤愤地说道。
“那不就得了?”玄奘微笑道,“这就说明全世界的人不会都当和尚,至少还会剩下一个。”
丹参被这句话噎得哭笑不得:“剩下我一个,难道会有子嗣?”
“林小施主也不会出家的,”玄奘淡然道,“你当出家是很容易的事吗?朝廷下发的度牒本来就少,女众更是凤毛麟角,轮也轮不到她的。”

丹参呆了一呆,恍然大悟:“哦……所以你才忍心顺着她的话说,因为你知道她根本就出不了家!”
“不,玄奘确实觉得,如果她真心出家,于她是件好事。不过,如果她是赌气这么做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玄奘站在窗口处,望着从房檐上垂挂下来的雨帘,淡淡地说道:“再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菩萨下生凡间,成为弥勒尊佛,度生无数。那时娑婆世界所有众生都修持十善业;那时人寿八万四千岁;那时山河大地一马平川,自然谷物应时而生,世界变得极为庄严殊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众生修持十善的共业所致。”

说到这里,玄奘回过头来,目光灼灼地看着丹参:“居士你想想看,只是修持十善业都会导致世界如此变化,如果大家都出家,修持沙弥戒乃至比丘戒,又会怎样?”
丹参不禁一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告诉你,那时这个世界就是娑婆净土!是一个以你目前的知识和经验无法理解的,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涅槃世界!一个不生不灭的世界,一个不垢不净的世界,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一个没有轮回的世界!你还担心没有子嗣?你很喜欢六道轮回吗?”
“你说的这些都是想象,我不信。”丹参不耐烦地打断他道,“除非你证明给我看!”

“你所说的人类会灭亡的场景,难道就不是想象吗?”玄奘反问道,“你又能否证明给我看?”
看到丹参被噎住的样子,玄奘又道,“其实,想要证明我们谁说得正确倒也不难,你可以叫全世界的人都出家试试。”
“这还不难?”丹参瞪着眼睛道,“这我怎么能办得到?”
“你既然办不到,还问什么呢?”玄奘道,“你自己都知道让所有人出家是办不到的事情,那你的担心岂不是杞人忧天吗?”
丹参先是语塞,随即又反应过来:“那么你来!小和尚,你让所有的人都出家,或者都修持十善业,以证明佛没有打妄语!”
玄奘摇头道:“我也做不到,因为我只是一介凡夫。我知道娑婆世界的众生还没有这份福气,所以我压根儿就不会问这种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说到这里,他将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那越下越大的雨,沉声道:“在这个世界上,玄奘唯一能掌控的就是自己。我希望命终之时能够得生弥勒菩萨的睹史罗天,听佛说法,将来随佛下生,普度众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离苦得乐……”

“你还是先度一度你身边的人吧!”叶先生一步踏了进来,身上的蓑衣还在往下滴着水,“锦儿不见了!”
“什么?!”丹参“呼”的一声站了起来,“不见了?她到哪里去了?!”
“我若是知道,还用得着上这里来吗?”叶先生慢悠悠地说道。一转身,却见玄奘已经快速披上了蓑衣,忙问:“你干什么?”
“找她去。”玄奘简短地回答了一句,便一头扎入雨中。
“等等,我也去!”丹参也冲了出去。
参见《四分律》,波罗夷,指戒律中的根本罪或极大之罪,犯此类戒者要被逐出僧团;僧伽婆师沙,又名僧残,指比波罗夷轻一些的罪行,意思就是犯此类戒者还有残余的法命;不定,是指已经犯戒但犯戒程度还不明确的行为;舍堕,是指由于贪心而追求财物的行为;单堕,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小戒;波罗提提舍尼,意译为“悔过”,是轻微的过失,主要涉及饮食等方面的规定,犯此戒者只需向一僧忏悔即可;众学,是较轻的过失,所涉及的是有关服装、食事、威仪等极细微的事情;灭诤,是为裁断有关僧尼犯戒等之诤议而设的七种方法,称之七灭诤法。 关于弥勒下生的时间,按照佛经中的时间概念,睹史罗天的一天相当于人间四百年,而弥勒在睹史罗天的寿命是四千岁,按一年360天来计算,现在距离弥勒降世大约还需要五亿七千六百万年。玄奘这里说是56亿7千万年,是按照古印度的记数法来算的,印度的亿其实就是中国的千万。 涅槃是佛教中的一种没有烦恼,超脱生死的境界,是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灭尽,而仅余的一种圆满寂静的状态。涅槃是梵文音译,玄奘后来把它意译成“圆寂”,也就是具足一切福德智慧(圆),永离一切烦恼生死(寂),永远不再被烦恼生死所困扰,回复圆明寂照的本有心体,而获得一种纯善纯美的庄严解脱。至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只能被亲身做证的圣人们完全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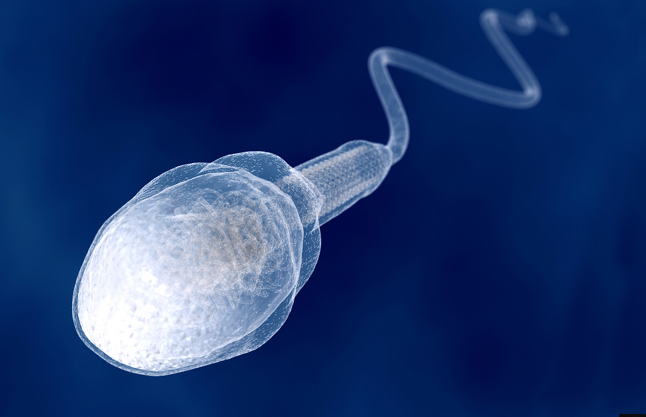
2、历史上玄奘法师的前世,大唐第一高僧玄奘法师
唐朝时,弥勒信仰盛行。玄奘大师晚年临终时,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弥勒菩萨处,而且也成功了,这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记载。
“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做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上面是玄奘大师的最后遗言,表明他发愿往生弥勒菩萨身边。
据经载,弥勒菩萨是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人物,释迦牟尼佛授记弥勒菩萨将来将会接替释迦佛成为娑婆世界的下一尊佛,现居兜率天宫内院。将在(有说56亿年)后降生人间成佛。根据玄奘大师的发愿,那时玄奘大师也会跟随弥勒佛下生,广做佛事。
玄奘大师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他与皇室的微妙关系、繁重的译经工作,都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感应,玄奘大师预感到自己的归期将至。那么,他在人世间的最后生命时刻,都做了些什么呢?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大师六十五岁,他依然在玉华寺翻译佛经。在这一年的历史记载中,有他对译场的助手和弟子们说的这么一句话:
“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
意思是说:今年我六十五岁了,一定是会死在这座玉华寺里,佛经数量巨大,我经常担心翻不完,你们大家加把劲儿,努力一点,不要怕辛劳。
在玄奘大师的一生中,他第一次发出了这种不自信的、怕自己的工作无法完成的担忧之辞。实际上,由于多年劳累,在翻译完《大般若经》以后,他自己就觉得体力开始衰竭,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就木。
不久,他又对弟子们说了一段话,几乎可以看作是他的遗言:
“若无常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可以蘧蒢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

他在这里提到了“无常”(僧人讲死,多以无常代之),说我无常以后,你们在送我的时候,一定要节俭,不要用很多的礼节,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裹送,把我安置在僻静的地方,不要靠近宫室和寺院。他认为肉身是不净的,应该远离这些地方。
同年正月初三,玄奘大师的弟子恳请玄奘大师开始《大宝积经》的翻译,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佛经。玄奘大师在勉强翻译了开头的几行以后,突然停了下来,他犹豫了很长的时间,平静而凝重地看着他的弟子,神色黯然地对大家说:“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

他说:这部《大宝积经》的分量不亚于《大般若经》,我自己觉得我的体力和精力已经不足以再翻译如此大部的佛经了,“死期已至”,不是“将至”,而是我的死期已经到了,不远了。说完这句话以后,玄奘大师从此绝笔,停止了翻译工作。他表示,要把此后可以预见的很少的岁月留给自己去礼拜佛像,为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做好准备。
正月初八,玄奘大师的弟子之一玄觉法师,梦见一尊庄严高大的浮图(即佛塔)突然倒塌而骤然惊醒,他担心这个梦是自己会出什么事的征兆,于是赶紧就去找他的师父玄奘大师,请玄奘大师解梦。
玄奘大师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非汝身事,此是吾灭谢之征。”意思是说:这跟你没关系,而是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征兆。
这是对正月初八玄觉法师做梦的真实记载,我们后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道理去揣测、去枉自判断其中的真假,因为高僧是不打诳语的,这是戒律规定的,更何况他们对玄奘大师又那么崇敬。

仅仅一天以后,正月初九,曾经翻越过无数崇山峻岭、曾经跋涉过无数滔滔江河都不在话下的玄奘大师,居然在屋子后面跨越一道小小的水沟时摔了一跤。虽然只不过是稍微擦破了脚腕处的一点点皮而已,玄奘大师却从此倒下,病情急转直下。
正月十六,玄奘大师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口里喃喃自语:“吾眼前有白莲花,大于盘,鲜净可爱。”说他见到了很大的白莲,比盘子还大,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可爱。
第二天,玄奘大师又梦见在他住的禅房里突然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人,非常高大,身穿锦绣服装,在他禅房里来回穿行,院子后面的山陵之间突然布满了鲜艳的金幡、旗帜,林间奏响了各种各样的音乐,门外停满了装饰华丽的车子,车子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来供养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一面说:“玄奘未阶此位,何敢辄受?”一面却还在不停地进食。

弟子赶紧把玄奘大师叫醒,玄奘大师睁开眼睛,把自己刚才看见的事情告诉了随时等候在他身边的玉华寺寺主慧德法师,而这个寺主非常恭敬的把玄奘大师的这些描述记下来,留给了后人。
玄奘大师同时还对慧德法师说:“玄奘一生已来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并不虚也。”玄奘大师的意思是说:我在梦境当中看到的这些现象,好像表明我这一辈子所修的福慧没有白费。我确信,佛教因果不是虚妄。
在生命弥留之际,玄奘大师作为一代高僧,还在竭尽自己最后的精力印证佛法,这是一个高僧修行的一部分,是他的功课。
当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下令自己的弟子,把已经翻译完成的佛经编一个目录,看看到底翻译了多少。统计下来,从西天求回来的佛经还有五百八十二部没有来得及翻译。实际上这已经是玄奘大师在做自我总结。

玄奘大师又吩咐众僧,为他造像写经,广为施舍,同时他按照佛教的戒律,把自己用的东西全部施舍给寺里的僧众。
玄奘大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容不迫地等待着圆寂时刻的到来。那么玄奘大师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刻,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什么?玄奘大师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圆寂的呢?
从记载上来看,这以后玄奘大师的病情似乎稳定了一段时间,或者也就是世俗所谓的“回光返照”。
在正月二十四日那天,玄奘大师还很清醒,他让一个叫宋法智的塑像工人,在玉华寺的嘉寿殿竖起一个菩提像,把骨架搭好。

他召集了所有身边的翻译佛经的弟子,留下了在人世间最后的话:“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做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玄奘大师说:我自己的俗身是不净的,这个俗身我已经厌恶了,我在这个世间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不必要再待着。我不是为我玄奘个人修福慧,我修的这一切我愿意把它回报给人世间仍然活着的人。我祈愿,我能跟大家一起上生到弥勒菩萨身边,去奉侍弥勒菩萨。我发愿,当弥勒佛下生的时候,我愿意跟着他下来“广作佛事”,去追求无上菩提,追求最高的智慧。
这是玄奘大师最后成段的话,也是他最后的发愿。
在接下来的日子,玄奘大师几乎就不说话了,只是不停地念诵佛经,皈敬弥勒、如来,愿往生弥勒净土。我们一般讲“三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玄奘大师肯定比我们多了一皈依,即皈依弥勒佛。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不停地吟诵的,我们在今天依然可以复原,他一定是不停地在吟颂皈依,他一定是在用佛当年所使用过的语言——神圣的梵语,不停地在复诵着皈依。
二月初四夜开始,玄奘大师右手支撑着头部,左手舒放在左腿之上,非常平缓地,右胁而卧,再也不动半分了(以右手而自支头,次以左手申左髀上,舒足重累右胁而卧,迄至命终竟不回转)。这是玄奘大师圆寂前的最后姿态,也就是玄奘大师肉身的最后姿态,我们看见卧佛就能想到这个姿势。
二月初五夜半时分,他的弟子问玄奘大师:“和上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看见玄奘大师那么长时间一直在念诵佛经,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弟子问玄奘大师,和上(“和尚”在佛经中是个尊称,但自己不能称自己为“和尚”,只能称“贫僧”或者“小僧”,而最尊敬的写法应该是作“和上”),您是不是已经决定可以生到弥勒佛净土呢?

玄奘大师回答说:得生。
这是玄奘大师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两个字了。
玄奘大师十三岁皈依佛门,二十八岁只身一人远赴西天求法,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求得真经返回祖国。十九年的留学生涯,十九年的译经弘法,玄奘大师终于求得正果,安然地去了自己一生所向往的弥勒佛净土。当玄奘大师圆寂的消息传出之后,唐朝的帝王和百姓们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唐高宗在二月初三得到玄奘大师因损足得病的消息,初七就派御医带着药物赶往玉华寺。等御医带着皇上亲赐的药赶到的时候,玄奘大师已经停止了呼吸。玄奘大师圆寂的消息传到长安,举国悲悼,唐高宗哀叹:“朕失国宝矣!”甚至为了玄奘大师而罢朝数日。
第二天,唐高宗又对群臣提起这件事:朕国内失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亦何异于苦海方阔,舟楫遽沉;暗室犹昏,灯炬斯掩!

二月二十六日,唐高宗下旨,玄奘大师所有丧事费用由朝廷负责。三月初六,又下令暂停翻译工作,已经完成的部分由政府出资传抄,尚未完成的交慈恩寺保管,不得遗失。可惜的是,后来绝大部分经书几乎全部遗失。
三月十五日,唐高宗又一次下诏:玄奘大师葬日,宜听京城僧尼造幢盖送至墓所。皇帝特许玄奘大师下葬的那一天,京师所有寺庙造的各种旗帜、宝冢、伞盖等送到玄奘大师的葬地。玄奘大师的灵柩运回京城,安置在慈恩寺翻经堂,每天前往哭墓的僧俗人数成百上千。
四月十四日,按照玄奘大师临终前的心愿,将他葬于浐水之滨的白鹿原,这个地方在万年县东南二十里,当时五百里之内赶来送葬的人不计其数。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迁葬到樊川北原(今西安附近),并在当地营造塔宇寺庙。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又下令在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各建造一座佛光寺,追谥玄奘大师为“大遍觉法师”。

这些都足以看出玄奘大师的地位和声望。在玄奘大师圆寂后一百八十年后的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一场法难——会昌法难,由统治者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一切寺庙,淘汰僧尼。而就在这样大规模的会昌法难中,长安的慈恩寺则被明令保留了下来。就这么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玄奘大师的功德和声望。
本文关键词:玄奘法师之前世今生,玄奘法师前世是佛陀哪位弟子,玄奘大师的前世,玄奘法师的原名,玄奘法师身世。这就是关于《历史上玄奘法师的前世,国人不该遗忘“千古第一人”》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