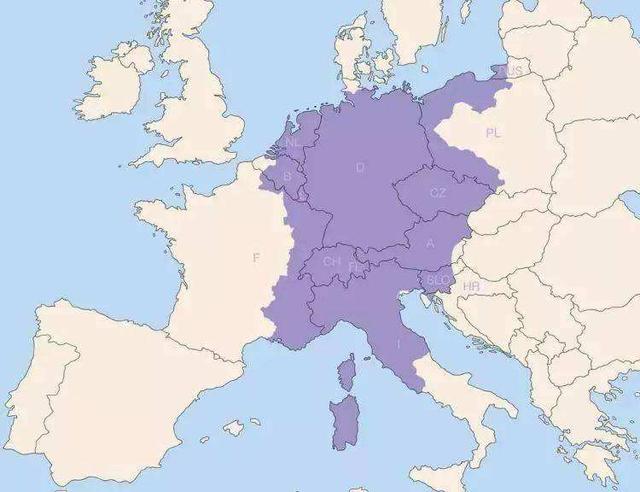“快点起来,赶凉早点去将畈上的谷割了”。炎热夏夜,上半夜热浪滚滚难以入眠,后半夜才刚刚眯着被母亲叫醒了。虽然心里极不乐意,还得爬起来,跟着父亲出发了。
星星还在眨巴着眼睛,路边的野草还带着露珠。一路上,可以听到附近有早起的人家割稻的声音,还有人吆喝牛的声音。自家的责任田里,金黄色的稻穗看起来都很饱满,沉甸甸的低垂着头。父亲看到这丰收的谷子,欣慰地笑了。
这块田大约有二亩左右吧。蚊虫特别多,稻禾的叶子也疹人,必须穿长袖长裤才行。十来岁的我双脚一下到田里,就感觉陷在烂泥巴上了,换位置时需要用力拉才能将脚拔出来。就这样割了一个多小时,天才慢慢亮起来。母亲带着她用小麦粉做的粑和茶来了,我的肚子饿得呱呱叫了,就和父亲坐在田塍上吃起早餐来。
太阳慢慢出来了,田畈上都是忙着耕作的家庭,有割谷的、有用牛打草滚的、有扯秧苗插田的。大人们在劳作之时,隔着田塍偶尔相互闲聊几句,神情中抑制不住丰收的喜悦。天开始热起来了,我和父母三个人连忙抢着割起来,总算在十点前将这块大田割完了。顾不上休息,我们将割下来堆放在田里的稻禾抱到田塍边,让太阳晒干点,然后捆了两担稻谷挑到禾场占地方。
稻谷被捆起来后叫“草头”,一担草头重十几斤。二亩稻田至少要捆六十多担草头,稻田离湾子有一里多路,父母亲挑起一百多斤的草头来回三十多趟,直到天黑了总算挑完。
稻禾挑到了禾场上,必须将谷子连夜脱粒出来,否则会发酵变质,那就不好吃了。父亲抱着一捆草头放在长凳子上,我和母亲每人一根棍子轮流用力打,打完了上面,父亲就将草头翻过来打下面。我和母亲都要仔细地打,一百多捆草头打完,人都要散架了。
虽然每捆草头被我们仔细地打了一遍,还是有三分之一的谷粒在稻草中没有脱落,父亲将这些草头堆叠成一个两米高草垛,等空闲的时间,铺在禾场上,用牛拉着石磙压上几遍,谷子才算全部脱粒完成。
这一切收拾好,已近半夜了。喧闹的村庄慢慢宁静下来,干完农活的家庭,都先后将竹床搬到禾场上,孩童们闹着玩了一会后就睡了。没有电扇,也没有蚊香,每一个家庭都睡的非常香甜,因为他们实在太累了。
从割谷开始,到插田结束,这样高强度的“双抢”劳动,基本上是连轴转的劳作,人手多的家庭要忙碌一个多星期才能完成,劳动力少的则要十天半月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刘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