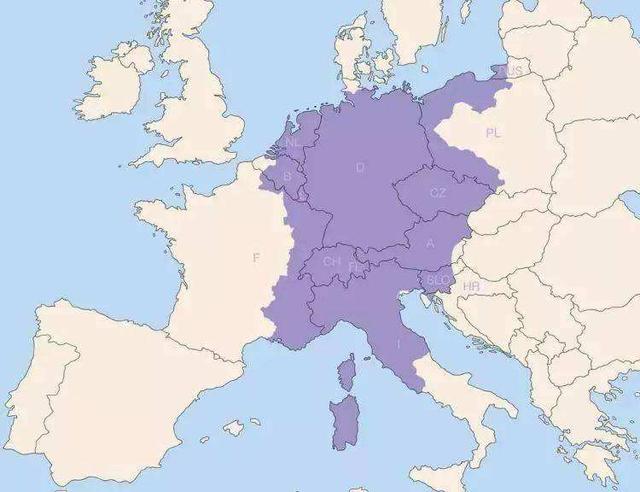○程时文
东楚网黄石新闻网(黄石日报)父亲的背影一直在我心中。
我的老家坐落在鄂东绵延起伏的山褶皱里,身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带领全村青壮劳力去十里八乡修水库、修公路;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走几十里的山路;扶起犁耙风里来雨里去在田间辛勤劳作。
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后,父亲显得更加忙碌。那年双抢季节,我请探亲假回家看父亲,翻过那座熟悉的山,我家的那一份责任田呈现在眼前。在明晃晃的太阳下,父亲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背上,一条条汗渍沿着深深的褶皱流湿了他那宽大的青布短裤,父亲正扬鞭叱牛在辛劳耕田。
望着父亲的背影,我仿佛看见一株壮实的禾苗正把根须深扎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吸收着营养长高、长大;望着父亲的背影,我似乎看到他宽宽的额,额上那或深或浅的皱纹,是他在坎坷的岁月里编织的密密麻麻的希翼。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进城参加工作的那天,父亲说啥也要送我,他固执地要为我背简陋的行李。他在前面默默走着,我望着父亲的背脊默默跟着。被春雨湿透的田埂路格外湿滑。一路上,父亲都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几次回头,嘴唇颤抖着,竟没说出来。
小镇分别时,父亲紧攥着我的手,父亲的手是温暖的。车启动了,望着春雨中伫立的父亲的背影,我鼻翼一酸,我陶醉在深沉的父爱之中。
其后几年,我和弟弟妹妹一个个成家立业,按理他可以好好享受享受。可他却说:“田地是我们农家的命根子,丢不得。再说,我这身子骨还能再干两年,等动不了时再说。”
一年,父亲好不容易从乡下来看我,可刚住了三天就嚷着要回去,说是住不惯这高楼大厦,“鸽子笼似的,闷得慌”。又说那两亩责任田还等着他回去施肥,耕牛也等着他回去喂草料。我终于没能留住父亲。听乡亲们说,父亲去世的头一天,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竟不顾乡亲们的劝阻,拖着重病的身体,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到村前的田野上。晚风吹拂着父亲的银发,他默默地看着与他朝夕相处了大半个世纪的田地,看着田里一个劲疯长的庄稼。在夕阳的映照下,父亲的背影犹如一尊挺拔的雕像。
父亲的背影,是一本厚厚的书,简陋的封面,里面记录着人生的酸甜苦涩;父亲的背影,是一颗平凡的星,在繁星闪烁的夜空里保持着自己的本色;父亲的背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辛勤的汗珠里闪耀的是动人的色彩;父亲的背影,是一首无字的歌,流动的旋律里弹奏的是悠悠的岁月……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世事怎样沧桑,父亲的背影啊,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宽阔的大海,不改的青山!